
△小帆自述:汪帆,人称汪小帆,70后修复师。每日坐山观湖,算不上心灵手巧,却沉迷修复无法自拔,偶尔出去当当背包客,顺带访访纸。尤好旧时光里的小物件儿,偶有所得,其乐也融融。闲暇时爱拽点小文字,写不好论文,却好用轻松笔调扯扯修复生涯中的人、事、书。
8月12日,人还在访纸途中的四川白玉县,提前预备好的《书叶翩翩》连载四,又准时发了出来。其实,在交第三篇连载的时候,我就偷偷地跟赵洪雅老师说,因为要外出访纸十余天,期间恐怕无暇写稿,所以请把第三篇和第四篇刊出的间隔时间拉长点,以保持每周一篇的频率,就会显得我是准时交作业的。赵老师很是善解人意,告诉我没有关系。可我内心总是惴惴不安,答应好一周一篇,失约总不太好。

从川北回到杭州,心还在藏区高原上飘着,脑海中北川的洪水还未退去,惊魂未定,又沉浸在杭州潮湿闷热的空气中,忙碌着“棹湖孤山,问津琅嬛——庚子晒书雅集”辅助工作。待一切忙完回神后,《书叶翩翩》已经开了两周天窗,接下来写什么呢?心里还是一片茫然。不由得又想起2008年在北京培训时杜伟生老师曾跟我说的话:李致忠先生每天都坚持写2000字左右的日记(或者是读书笔记吧,时间搁久了记忆有点模糊),若是你也能如此坚持记录修复心得,未必写2000字,就是500,甚至200字,天天坚持,若干年后成果也不可限量。当时听得热血沸腾,备上精美典雅的笔记本数册,只待泥雪留鸿迹了。然而,若干年倒是过去了,成果却不见有:翻开那些笔记本,前面数页,字迹工整,待到后面,龙飞凤舞,其余绝大部分都是空白页。想来,真能按杜老师所言,坚持做笔记,现在拿来写《书叶翩翩》系列,也不至于如此犯难。

这几天杭州的日头感觉依然炙热,早晚的空气中却多了一丝凉意,所谓“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也正当时。夏日未过,荷花依旧,而行人却已回首寻望四野,不看姿色只觅秋香了。诗人爱的就是这种隐隐绰绰的幽香,我却喜欢院内空气中那种不动声色,却又如影随行的甘味。若平日里,登上青白山居藻思阁阁楼上的中央纸库取纸,这般直上登临毫无曲线之美的连续台阶,加上搬运劳作的事,总是能拖则拖。但到了这个季节,如能拾阶而上,满身心沾着这丝丝甘甜,攀登与劳作就不会感到那么辛苦,反倒有如小半个时辰的登高望远一般,心旷神怡。一入阁楼,大自然的气息就被挡驾在纸库门外,扑鼻而来的,是松木纸柜散发出来的木头材质的清香(其实松木的油性比一般的木头要重,并不适合用做纸柜,当时制作时,不懂这些门道,借此记之,引以为鉴),且清香之中又夹杂着各种纸的味道。纸真的是有味道的,那是乡土的胎气、山水的滋味,特别是刚从密闭的包装袋取出的一瞬间。其实纸味很难形容,特别是几十万张放在一起的纸,味道更加纷杂,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过,我总是闻之心安,犹如见到老友一般亲切。据说,佳肴有三个标准:色、香、味俱佳。一纸问世,天生有色、有味,染纸的植物染料更具清新之味;印成书籍,又添墨香与文化的熏染。所以,在古籍修复师的眼里,每种纸都是供选的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

这次上楼选了些八十年代产的福建毛太纸带出纸库,我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提到过它们:当年购买的时候价格实在太便宜、存的时间又够久、好用。遗憾的是,现在毛太纸早已无人生产。纸库内硕果仅存的虽下不了手选用,可再不舍得也要用。修复康熙年间的《杭州府志》,书叶纸薄,风化颜色变深,得上楼从二十多万张毛太纸中选点特别薄的去染色。染色后的纸,略略会比未染色的厚一点,硬挺一点,修复《杭州府志》倒是恰适其用。挑挑捡捡选定了两叠纸,一般情况下,我们用“刀”来形容纸的数量,一刀是100张。可偏偏福建的这批毛太纸是160张一叠。记得有一次去江西访纸,纸坊老板告诉我,他们这里一叠纸是 99张,这是多年传下来的习惯,100张纸里必定会抽出一张,或卷烟、或当手纸,总是不能让它足数,其中的原因,他也说不清道不明。我更不知道这毛太纸的160张一叠有什么说头,上回去福建访纸,因没找到生产毛太纸的人,也就没法问出个所以然来,希望有机会有人能帮着解读解读。

抱着纸回到修复中心,里面弥漫着一股中药的味道,看来同事们已经把橡椀子给炖上了。“炖”,是的,我们喜欢用“炖”这个字来形容我们提取植物中的色素制作染色滤液的过程。这“炖”出来的有色汁液用来染纸,以使补纸的颜色更贴近待修古籍的纸色。所以,这“炖”字,便有慢火精心熬制的意味:炖出的是植物的精华,染出的是古纸的旧颜。在炖的过程中,先把橡椀子洗净,剔除杂质,用水盖没它,然后用大火烧开,再调小火候,慢条斯理地让它在锅里炖上一个小时,待到把内核里的色素都给炖出来,大约也就差不多了。有时候,需要深点的颜色,得炖更久点,甚至炖完后仍搁在锅里过夜,待第二天,颜色就会更浓郁些许。除了橡椀子外,我们常备的还有红茶、熟普。红茶炖出红棕色滤液,有些书叶边缘部位风化后发红色,就可以用它来染色,但它的稳定性差,容易变色:染得接近纸色吧,没过多久,它就深过了书叶;染得过浅吧,看着又不和谐。使用的时候拿捏的尺寸确实难把握,况且不同品种的红茶,出色还不一样。有一次库存红茶用完了,我们换了一个新品种的,结果,怎么染都是偏黄棕色,就是出不了那抹红头。无奈,最后换成熟普才算了事。至于黄蘗和栀子用的就很少,但也并非不用。几年前,我尝试用黄蘗染纸,结果染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黄绿色,被同事们笑了好久,只好扭扭捏捏地把它塞了箱底。前段时间,碰到修复一个家谱,扉叶就是黄绿色的,灵机一动,把塞了箱底的那张黄蘗染的纸翻出来,稍加加工,“废物”也派上了用场,倒省了许多事。栀子出的色太过鲜亮,估摸着得跟其它颜色配着用才合适。我们的经验是,各种各样的染色原料,都是要备着点的,要学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中华古籍如此庞大的数量,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碰到千奇百怪的颜色呢?其实修复师还真不怕修书,就怕配纸、染纸。有时候光染纸就能染上好几天,才能出个理想色。而最怕最怕的就是修了一半的书,突然发现染色的纸不够了,需要补染纸,要追色就特别难了,出来的颜色因原料品种、蒸煮时间、染色对象、甚至天气温度的变化而产生无穷之变化。吃过几次苦头后,我们也就变聪明点了,每次找准颜色后,煮上一大锅染液,倒在一个特制的大口长方形平底盆里,各种常用纸张,都分类往里摆放。纸张轻薄,浮在染液上,用手轻轻施以压力。看着纸面浸入染液中,里面的空气吐着泡浮上来,颜色似乎钻入了纤维中,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浸泡时间当然与染色深浅、纸张强度、纸张数量密切相关,目测颜色差不多了,就把它们一一拎出染液,控水、搭在木杆上晾挂。听着滴嗒之声,时不时的瞄上一眼,等纸张六七分干时,把它一张张揭下,分别晾干。纸全都干透了,喜滋滋的把它们收拾起来,再分类放到纸柜里,整个心情不亚于粮食丰收时的庄稼人。

几年前,有一个搞书法的朋友请我帮染一张磁青纸抄《心经》。我用刷染法染纸,既要考虑颜色的均匀度,又要思忖手法的轻柔度,一张四尺三开的小纸,道道叠加,层层晕染,由月白至浅蓝、花青、湛蓝,自己也不记得染了多少遍,总算出了一个我们都满意的颜色,深沉而典雅。这些功夫可不是白花的,所以近几年,市场上出现了纯植物染色的封面纸,一张四尺整张的要价三、四百,有人惊呼天价。但我认为,需要的时候是真值得,数十道工序下去,其效果哪能是市场上几滴化工染料可比的?只要贵得有道理,那就不能算贵。

前两天,与一个朋友聊及非遗传承为何如此之难,他认为,技术不统一不量化,导致传播之困难,他希望我们这些手艺人,能够让行业透明,唯有如此才是对一个行业的最好保护。我拿染色工作与之辩驳,而他却提出减少变量,通过设备手段控制室温、湿度,佐以配色卡,比对配色卡做颜色调整,并做好记录数据。他的想法虽有难度,却并非不可能,只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以现代化的手段去推进,亦或依然墨守成规,完全凭感觉行事,就如烧菜时,投盐多少一样。当然,后者只是关系到口味的小事,而传统技艺却是牵连到生死存亡的大业。面对他的诘问,我百般辩解,却无法反驳。诚然,这些工作虽然难,却正是我们应该做的正事。

杜伟生老师数次跟我们提过,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曾见到修复人员在修复一册图书需要染纸配色时,便从该书的书盒中取出一张纸,上面记录着1925年此书修复时使用的染色颜料配方。这张并不起眼的配方档案,为数十年后的修复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操作依据。故,每次染色加工时,都必须记录染料配方存档,这是修复工作记录的一部分,也是修复历史的见证。
由此,我又不禁想到杜老师要求每天写500字笔记的事,若是当年真能如此,是否真的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技术都量化和显性化呢?我不知道,因为,13年过去了,我的笔记本还是空了大半的。这空了大半的笔记本,又怎“遗憾”两字了得?
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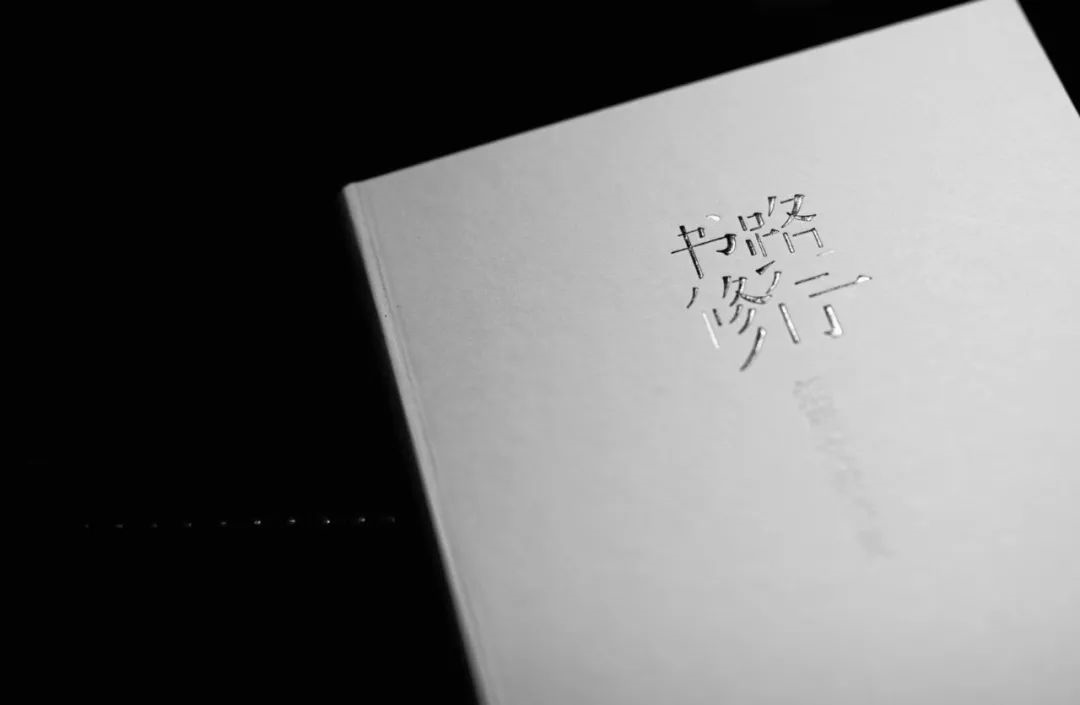
《书路修行——纸质文献修复》
著 作 者 I 汪帆 李爱红
出版社 I 西泠印社出版社(杭州)
本书汇聚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专业修复师汪帆十年修书心得,从纸质文献的概念及分类谈起,概述纸质文献保护与修复历史,解读纸质文献的修复原则,对纸质文献的修复空间及设施设备、工具、材料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对纸质文献的修复技术做了精辟的阐述,并列举了丰富的修复实例及教学案例。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汪帆还对未来纸质文献保护与修复做了发人深省的思考。该书将以古籍修复的理论与修复实践相结合,将纸质文献修复的常识与战略思考相结合,既深入浅出,又具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是一部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古籍修复佳作。 (文 I 姚伯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