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代史讲座“稽古·贯通·启新”讲稿《忧患与繁荣——宋代历史再认识》下篇。更多精彩内容,敬请阅读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编《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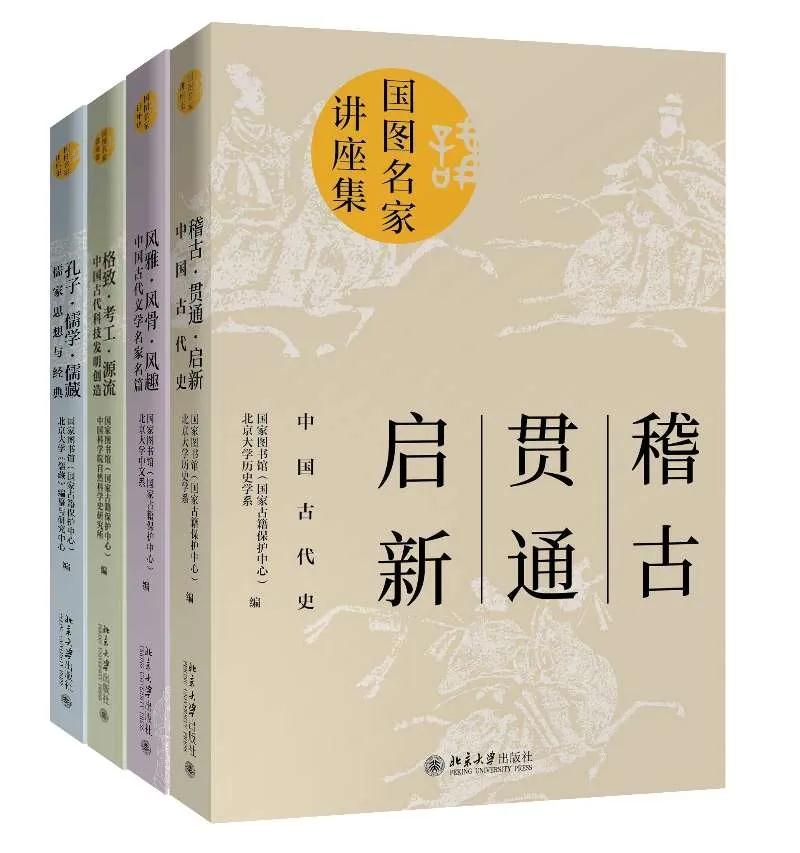
《国图名家讲座集》(全4册)
二、“立纪纲”“召和气”:相对开明的国策基调
宋太祖在公元960年的时候,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现在我们回头看,会觉得宋太祖赵匡胤是“大宋”王朝的开国君主, 但跟他同时代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新上台的皇帝呢?
宋太祖是接在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朝代后边宋代的第一个皇帝。五代一共有14个皇帝,总共在位54年,每一个皇帝平均在位多少年,一目了然。每一个皇帝上台以后,都希望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实际上是像走马灯一样更迭得非常频繁。这14个皇帝里,开国君主大多原来是军队的统帅,靠着部队的实力推翻了前面的皇帝,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当时的君主。现在赵匡胤又上来了,又是一个军事统帅,又是这样摇身一变上来的皇帝,当时的人有什么道理相信他会是一个长期维持的王朝的开国君主?我想当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前面的五代过去了,现在短命的六代、第15 个皇帝又来了。但是赵匡胤创建的这个王朝最终巩固下来了,宋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有320年的时间;所以后来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宋太祖能“易乱为治”,把扰攘混乱的局面转成为相对平稳。南宋大儒朱熹也和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学生说“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 他回答说:“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朱熹告诉他们,宋太祖只是把五代最不合理的措置去除了,而其他枝节的法令条目暂且延续不动。然后朱熹强调说:“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
赵匡胤当皇帝17年,还不到50岁就非常突然地去世了。他去世之前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一个24岁,一个18岁,但这两个儿子都没有被指定为太子。赵匡胤去世以后,他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就是宋太宗。宋太宗上台以后,表示要继承太祖的事业,他在《即位诏》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事为之防, 曲为之制”这八个字,是宋太宗对他兄长所作所为的一种提炼。“事为之防”,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防范,事发之前就要考虑可能的后果,而不能等问题出来之后再去堵窟窿。“曲为之制”的“曲”就是委曲周全的意思,要周全地设立制度,进行制约。这八个字放在一起, 就是现在说的防微杜渐,所有的事情要防范在前。这应该说是宋太祖防范弊端非常重要的行事方针,或者说是指导思想,宋代的朝政里始终遵奉着这样的原则。
帝制时期都是专制的时期,专制时期都谈不上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但是专制也不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专制的方式、程度也有不同。宋代的朝政应该说是中国历代王朝里面最为开明的。有两个小例子,都是讲太祖朝的。“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沈括《梦溪续笔谈》)宋太祖是军旅行伍中摸爬滚打上来的,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有的时候没有文化的人问出来的问题,有文化的人反而很难回答。赵普想来想去不知道要怎么答,皇帝一直追着问,最后赵普只好说“道理最大”。道理是最大的,能够笼罩住天下所有的东西。皇帝觉得不错,十分称赞。赵普跟宋太祖究竟是否有过这么一个对话,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宋人相信是有的,宋代不少文章、奏议里边提到这件事,认为“道理最大”这样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另外一件事情还是说太祖。“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详。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宋曹勋《松隐集》卷二十六)这一件事情、这么一块誓碑到底有没有,我本人高度怀疑。但是从宋代的做法来说,可能确实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在处罚、诛杀大臣的时候,宋代皇帝是比较小心的。给皇帝提意见的人,宋代有不少因言治罪的,但是极少有因为言论而被直接处以极刑的。这种情况和其他帝制王朝很不一样。宋代也有文字狱,有党同伐异的事情,比方派别之间的争斗,以整倒对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但是总体上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思想相对比较自由,言论也比较开放,我们会感觉到当时议论勃发的情形。因此陈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论〈再生缘〉》)
宋代是一个求稳定的时期,因为外部的压力很大,所以它内部求稳的特色非常突出。稳定也是要有一定的把手的,就像一辆车的轴或者两个轮子一样,一端是“立纪纲”,一端是“召和气”。纪纲就是纲纪,也可以说是法制制度,欧阳修就把纲纪和法制连在一起讲,“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是以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可不戒哉!”(《新五代史》) “召和气”,王禹偁端拱二年(989)上太宗疏中提到“感人心,召和气,变灾为福,惟圣人行之”。当时人觉得天地之间运行着阴阳二气,如果阴阳二气都是自然的运行,人世间不对它有任何的干扰,那么就会感召和睦之气。宋代人很多言论、著述里边都将国家的仁政与和气联系在一起。这样,法制、纲纪和作为治国原则的道德仁义,这两者的综合就构成了当时追求平稳统治的基本路向。在一些具体的制度里也都能看到“立纪纲,召和气”的体现。
“立纪纲”就是要建立制度。以科举制度为例,宋代已经有了唐代的科举作为基础,中国历史上从隋炀帝的大业元年(605)开始到1905年结束整整是1300年的时间,曾经有学者统计这1300年里各个历史时期所取的进士总数,以及平均每一年的取士数额。科举考试跟现在的高考其实性质完全不同,现在经常把高考和科举相提并论,但高考选拔出来的人还是要进学校的,它是教育各个环节里边的一环,而科举不一样,它是假定你受教育的过程已经结束了,考出来的人是要去做官的。如果说这一年科举录取的进士只有一二十名,而当时的整个官僚队伍至少是有五六万人,这一二十名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投到五六万人的官僚队伍里边去,很快就被淹没了,不可能说去改变官僚队伍的素质。只有当它形成一定规模的时候,才可能对原有官僚队伍的素质造成一定的冲击。各个时代比较起来,宋代科举考试是取士最多的。唐代科举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宋代“立纪纲”,相关制度更加严密,也更加开放了。通常一个制度“严密”就不容易“开放”, 如果强调开放,制度往往就不够严密。而宋代正是通过制度的严密化, 才使其得以向更多的人开放。
唐代有“投状”和“温卷”,士子在应试之前,可以提前把文章给当时的达官名流看,以求推荐。科举考试之前,皇帝会临时指定一名主考官。比如《唐摭言》“公荐”条有这么一个故事:
(唐太学博士吴武陵荐进士杜牧,)曰:“请侍郎与状头。” (崔)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还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呉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 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这样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不合理,现在我们也说高考不要走独木桥,中学校长可以实名推荐。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保障, 就会让人对它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质疑。晚唐有位诗人叫杜荀鹤, 科举考试没有考中,作诗说自己“空有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 意思是,虽然我也有很好的文章,但是朝廷里没有人帮我推荐,所以考不中。这种对科举公正性的质疑,就会伤害这个制度的公信力。
宋代也有跟科举有关的诗作,“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 这是什么意思呢?考生科举应试都是要答卷子,在卷子上面写文章,卷子的最上边会写明考生的籍贯、姓名和祖宗三代。在唐代,考生的名字主考官是看得到的,所以崔郾很容易就把杜牧找出来。但是在宋代, 考生的卷子一交上去,监考官员就把名字糊住粘上了,这个叫“糊名”。糊名之后,拿《千字文》给他盖上一个号,就像我们高考的考号一样。后来考生的亲笔试卷要封弥存档,考官批阅的是专门请人另外抄过的试卷,以防考生字迹被识别,这叫做“誊录”。宋人会说糊名制度是很公道的。如果你家世背景“孤寒”,“孤”就是朝廷里没人帮忙支持,“寒”就是家里相对清寒,不是腰缠万贯——家里如果很有钱,不必来考科举,可以经商致富或者干很多别的事情;假如又孤又寒还想要出人头地, 做一番事业,只好去走糊名科举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比较公道的。
叶梦得《石林诗话》记载了一个跟苏轼有关的故事:
李廌,阳翟人,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举,廌适就试,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为廌无疑, 遂以为魁。既拆号,怅然出院。以诗送廌归,曰:“平时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苏轼弟子李廌元祐三年(1088)报名参加科举考试,正好这一年皇帝指定苏轼当主考官,宋代主考官被指定以后当天就要进贡院,贡院当天就锁门了,叫“锁院”。那个时候不能打电话、不能发短信,内外之间谁来请托,事实上就办不到了。不过苏轼对于李廌文章风格很熟悉,师生两人都觉得选拔出来没有问题。于是出题,考试。考完开始阅卷, 苏轼看到一篇卷子很高兴,认为肯定是李廌的,就把这份试卷放在首位。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主考官没有照顾自己朋友、学生的意图。所有卷子都判完了之后,开始拆号,结果第一名不是李廌,是章惇的儿子章援,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而苏轼基本上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但是名次不能改动了,所以这一年章援是省试第一。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共取了523个人,没有李廌。李廌很伤心,决定回家,苏轼就写了一首诗送他,说“平时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另外还有两句“青袍白纻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意思是说,这次来考试的有五千多人,我实在无法把你的卷子挑出来,我知道你当然不可能感谢我,可是你也不会因此而抱怨我。
我们看到,制度的严密化使得制度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是公平的,也就向更多的人开放。这样的“立纪纲”方式,实际上就达到了“召和气”的目的,也正是因此,宋代有一些“寒俊”(出身清寒的才俊之士)得以崛起。
过去有一出戏叫《状元媒》,里边的状元就是吕蒙正。《邵氏闻见录》卷八记录了他的一件轶事:
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后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书。公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饐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
类似事情,让我们看到宋代的风气跟唐代确实有一些不同。唐代很多人,哪怕是家境没落的,也总喜欢强调自己某代的前辈是做过大官的,而不愿意提及个人当年的贫贱。但宋人通常不讳言过去的清寒,渲染靠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
范仲淹当年也曾在僧舍里读书,他带去的口粮,要是顿顿吃干饭就坚持不到底,所以带去的米都是煮粥,到了冬天粥冻成一坨,就拿刀把它划开,一顿饭吃几坨都要计划着,家里带来的咸菜(“虀”), 也要分份儿吃,人称“断虀画粥”。范仲淹在寺院里边这样坚持了三年, 后来科举及第。我们知道,范仲淹本来是苏州范氏,但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山东,他是在朱姓人家长大,科举考试填的名字都是朱说。范仲淹做官之后回到苏州,建立了范氏义庄,支持范家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让他们能有机会去读书。
在那个时候,有一批这样的“寒俊”崛起。“寒”是指家境清寒,“俊” 是说本人是社会上的才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强调士以天下为己任,具有这样情操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上并非个别。这样一些优秀士人的代表,在当时既是政治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同时也担负起了一个时代道德主体的责任。
三、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下边我们来讲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宋代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刚才我们提到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期曾经提出“唐宋变革”的说法,我想我们不能把这种说法推到极端,不能说什么事情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延续和更革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从唐到宋确实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如果问不同的学者,他们会列举出不同的内容。如果从总括的角度、从整体的趋势来讲,或许可以用“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对它进行大致的概括。
我们说到“化”,都是指进行时。比方我们过去常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指一种进程,一种倾向,而不是完成时。有的学者说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区别于唐代的贵族社会,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如果说宋代社会是在走向平民化,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站得住的。另外它也有世俗化的趋向,包括当时的宗教信仰、思想文化、都市布局,都有世俗化的趋势。而且这一个时期对于“人”本身,对于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关心,我觉得比起前代来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这可以说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唐代的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之上建的,严整规范。它大体上是一种网格状的坊市型布局,宫廷在整个城市的北边,皇城紧挨着宫城,皇城是宰相和辖下各个部门集中办公的地点。唐高祖到唐太宗都是活动在太极宫,唐高宗、武则天是在大明宫,唐玄宗是在兴庆宫,基本上都是在城市的北边。城市里边有一个个方格状的居住小区, 这些小区在当时被称为“坊”,坊四围有坊墙,坊和坊之间有道路;大型的贸易集中在西市和东市。所以整体上来说,唐代长安城的尊卑秩序非常清楚,城市的功能区非常很明显。参加长安城发掘的考古系老师说,长安城布局如此严整,甚至让人觉得当时就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唐代一直到后期,城里边还是会有宵禁的,一到点,四处敲鼓,各个坊的坊门都要关闭,大街上不会有闲散的、游荡的人群。这样一种管理方式,相对来说比较严格,尊卑秩序井然,这是唐代长安作为一个都市给我们的基本印象。
宋代的东京开封非常不同。开封城最开始不是作为都城建设的。五代第一个君主是后梁朱温,他原来的大军区就在开封,摇身一变成为皇帝之后,就把大军区的司令部改成了皇帝的宫廷,宫廷范围从五代到宋代逐渐增扩。开封城的宫廷在城市的中间,这个位置与它当年作为大军区指挥部司令部的军事防卫功能有关。唐代后期已经开始有火器,用于攻击城市的手段更多了,如果宫廷是在城市边缘的地方,比方挨着北城墙,防守起来风险就会更大。因此,五代以来包括北宋, 它的宫城大内是在整个都城的中央,从宫城到内城到外城,是一个多重方城的布局。这个布局一直影响到后来的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其实也是这样,宫城即大内紫禁城是在城市中央,而不是像汉唐时期那样在城市的北端。
我们现在常讲要打破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界限,这就有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城市户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唐代中期以后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方方正正的小区,郭就是城郭,城市小区里边的这些居民就是坊郭户。到宋代,宋代的城镇居民、工商家庭都属于坊郭户,坊郭户固定为特定的户籍类别,出现了明确的户籍分野。坊郭户作为特定的法定户籍出现,说明那个时期城市居民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来进行管理。
宋代的开封,官府、民居、商户杂陈,城市空间、十字街头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面相和文化形式。比方说在《清明上河图》里,我们会看到不仅有沿街店铺,还有说书的老先生,有杂耍的、饮茶的, 熙熙攘攘的往来人群,在当时各种各样的世俗文化可以说是大放异彩。
袁行霈先生在《中华文明史》里说,中国文学到这时有了更加细腻丰富的表现方式。这一时期文学重心有着明显的下移,造成了文学的全面繁荣。文学重心的下移,首先指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唐代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唐以前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一个是文,包括骈体文、散体文,另外就是诗,一般来说士人才有能力从事这样的创作。宋代不仅仅有诗有文,文学体裁还扩大到了词,词是从青楼楚馆里面走出来的,有些文化人会去那些地方消遣,一边啜茶饮酒一边有人陪伴弹唱,以词填曲,就这样发展起来了。宋代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 这些都跟市井生活有密切关系,文学的体裁丰富了。
另外,创作的主体不仅是士族文人,还扩大到庶族文人和市井文人。市井文人指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是在明代形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早在宋代,街头上的说书艺人就已经在讲《说三分》,经过他们的传讲,三国故事越来越丰富化、细致化、戏剧化。这些人实际上都参与了文学的创作,他们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这些文学创作的结晶到后来形成了长篇小说。其他一些长篇例如《水浒传》也都是这样。与此相应,文学的接受者、欣赏者也扩大到了社会大众。
文学的风格与追求也有所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李白和苏轼都写过咏庐山的诗作,两首诗都是一流的作品,但是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意象是不太相同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非常豪迈,有一泻千里的豪情;苏轼的《题西林壁》看上去遣词造句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李白的这首诗,人们什么时候会想到呢?面对名山大川、面对着瀑布巨流的时候,好像会冲口而出诵咏李白的这首诗;而苏轼的这首诗,哪怕是在家中,在面对身边的世故人情时,都会引发我们的思考。所以钱钟书先生说,唐诗重在丰神情韵,而宋诗重在筋骨思理。
过去有人会说,宋人跟在唐人后面作诗是宋人的不幸,因为所有的好诗都被唐人作光了,但我们会看到宋人其实走出了另一条路。王安石有首六言诗《题西太一宫壁》,“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诗句题写在西太一宫这个道教宫观的墙壁上,多年之后王安石已经去世,苏轼看到这首诗,称“此老野狐精也”,实际上是赞颂王安石的过人才华。黄庭坚接续在王安石后面, 也题了一首六言诗,其中说:“风急啼乌未了,雨来战蚁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他和王安石在政治主张上应该说是处于两派的,但是这首诗表现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这些诗句,让我们从平淡中见到他们的追求,见到当时人崇尚的“理趣”。
杨万里的诗有些也用到平白的表述,印象中前几年开“两会”的时候,教育部的发言人讲到教育改革,引述了杨万里的诗《过松源晨炊漆公店》,“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发言人的意思是说教育方面虽然已经有不少改革措施,但是前边的路还长,还会有曲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诗和词是有不同功用的,二者表述的特长不一样。像李清照就特别注意这样的区别,她相对悲凉慷慨甚至愤懑的心境,可能用诗表现;而比较细腻委婉的情感,会用词来诉说。但是宋词也并不都是婉转含蓄的,柳永的词比较委婉,苏轼的词既有委婉的也有豪迈的。词作分为婉约派、豪放派,当时社会已经有些共识。词人柳永的名气很大,“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苏轼心里暗自不服,他当年在翰林学士院, 幕士里有一个人善于歌唱词作,苏轼就去问他:你看我的词跟柳永比较一下怎么样?这个幕士很会说话,他就说:“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郎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大江东去’。”(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苏轼“为之绝倒”,非常高兴。当时的人已经体会到,词的种类其实是很丰富的,给人们带来的情景体悟都是不一样的,丰富了情感的表达方式。
另外我们简单讲一下当时教育的普及。文化和文学的重心下移,跟教育的普及有关。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曾经在朝廷上跟皇帝说到“负担之夫”,就是以挑担负重为生的人(可以说是一千年前的“棒棒军”), 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家产,靠出去给人挑担子、打零工谋生,“微乎其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 谓之‘学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 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尚且要从微薄的收入中节省日用,为后代积攒上学费用,这些情况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对于读书的需求是很强烈的。他们不一定是想让儿子去考进士当状元,但是至少国家发的文告上说到谁家要交多少税,谁家有什么摊派,自己要能看得明白,不能受人欺骗。这样的一些孩子谁去教他们?当时国家官办的太学之类学校,某种程度上是为科举考试准备的预备班、强化学习班,有点像现在的“新东方”,不是从零基础开始启蒙教育的。农村下层民众的孩子, 学习基础普及的文化知识,主要靠的是分布于乡里村落的乡先生。虽然我们说宋代的科举考试录取数额历代最多,但是它的录取率其实不到1%,另外99%的参加科举考试而未被录取的人都要另谋出路。有一些会再去考,有的就转而耕读、经商、从医,或者做其他营生,包括去做乡先生。南宋的陈亮有一年没有考中,他就跟朱熹说,“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小秀才就是小孩子,这样边教书边复习,也挣一份自己的生活。陆游《秋日郊居》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说道他在乡下有一所房子,跟一座“冬学”挨着。农家的孩子平常不能去上学,大孩子在家里头看着小孩子,稍微大一点的要跟着大人下地,等到冬天地里没有活了,这些孩子才能去上学,这就是“冬学”。冬学里有一些老先生在教书,他们可能就是过去科举落榜的一些人。
有些科举落第者回归乡里,利用他们的知识、能力,或聚徒讲学,或影响公众事务,或成为乡里文化的普及者、基层社会活动的组织者。他们参与着不少村学、家塾,这些民间私学分布的时间、空间及其教学层次和灵活度,显然不是官办的州县学校以及书院所能比拟的。
现在说到启蒙教育的课本,都会说“三、百、千”,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实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顺序正好是反过来的。《千字文》是最早的,南朝时候就有了。《百家姓》中“赵” 姓放在第一位,赵姓人地位这么高,肯定是宋代;而“钱”姓排在第二位,在五代十国的时候,现在的苏州、杭州一带有一个小王国叫吴越,吴越的统治者姓钱,所以《百家姓》一定是北宋前期在江浙一带的吴越旧地出现的,只有那一带的民间才会如此尊崇钱氏。《三字经》则出现更晚,一般认为是南宋后期王应麟编的,明代以后又有改动。这样的民间教育,启蒙式教学,渗透到平民阶层,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最后利用一些图像来比较一下,我们说宋代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跟前代呈现出来的面貌到底有什么不同。唐代的画卷、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人物形象,大多是雍容闲适的(图四)。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唐代仕女俑,其实并不是上层贵妇人的形象,而只是普通的庶民、侍女,但是形象上非常自得,好像别无所求、非常满足的样子。再看看宋代的人物形象(图五),包括《纺车图》《货郎图》等画作,还有浮雕、砖雕、石雕里边的形象,我们会感觉宋代的这些人好像过得比较艰辛,都是忙忙碌碌的。以前就有学生问,是不是因为大唐是盛唐帝国,所以人站在那里都不用发愁;而宋代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每个人都挺辛苦。实际上,我想任何一个时期,下层庶民的生活都是很艰难的,都要经过无数的煎熬奋斗,只是唐代的画家、工匠觉得那样一种忙碌的形象不够美好,不值得呈现;而宋人相对比较关心下层庶民的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宋代受到中唐以来佛教禅宗的影响,所谓的“砍柴挑水,无非是道”,这种审美的观念,包括这种道理的观念,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也就是说,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值得关注、值得呈现的。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里边讲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通过雕塑、画作这样的一些可视的形象,也能让我们有比较清晰的把握。
究竟要怎么去认识宋代的历史?这个问题专门用一个学期来讲可能都讲不完,一个多小时里边能够讲的,只是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它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是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有很多突出的成就,在制度方面也有一些独到的建树。总体上讲,我们可以说宋代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牵动,使得它无愧为历史上一个文明昌盛的阶段。
最近这些年,跟我们国家“一带一路”这样的国际视野相关,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的时候反复强调,“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我想我们结合宋代的历史,对这段话也会有一些更加深刻的体悟。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