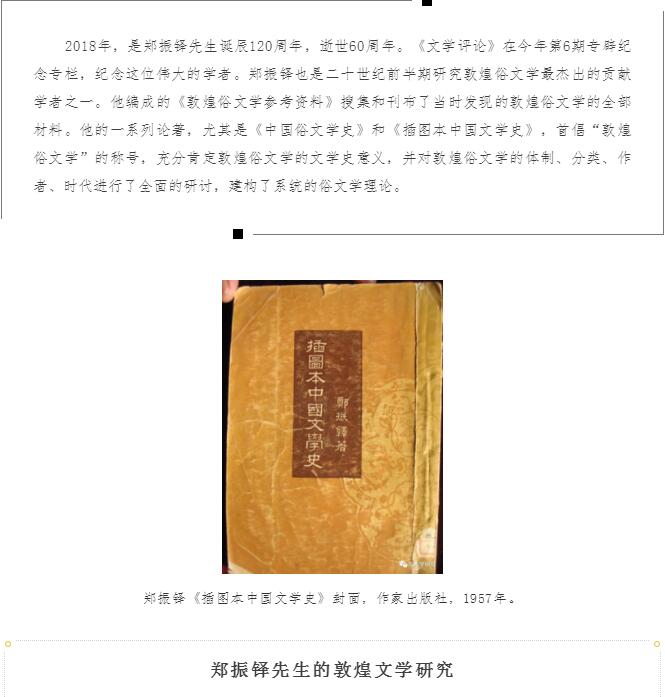
伏俊琏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福建长乐人。曾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等,1958年因飞机失事去世。有《郑振铎全集》20卷出版(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
郑振铎先生是著名学者,是中国二十世纪前期俗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先锋。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他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首先,他搜集和刊布了不少敦煌俗文学的资料,对敦煌俗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做了很高的评价。1927年,他流亡法国和英国期间,尽量利用时间查阅当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俗文学典籍。他说:“此次欧行目的之一,便是到各国的重要图书馆中,阅读他们收藏的中国书,尤其注意的是小说和戏曲。”“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竟见到了不少的中国的小说与戏曲。于是只想在那里小住几天的巴黎城,竟使我流连了几个月。”[①]数年后,他写了《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的长文,分宋元词集、敦煌文学、宝卷、弹词、鼓词、民间文艺作品、诸宫调、戏曲、散曲、小说、诗文集及其他文学要籍十一个类别评介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及价值。在其中《敦煌文学》一节中,他对近三十年来敦煌文学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情况做了全面总结,他说:“《云谣集》也充分的可见出古朴的原始的词的面目。韦庄的《秦妇吟》在质上是很伟巨的一篇名著,其复现于世,当然是最值得赞叹愉快的事。被疑为叶德辉氏伪作的白行简的《大乐赋》,也饶有民俗学上及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其实武进董氏曾先以柯罗版印出,叶氏仅就此影本翻刻。)长篇的叙事歌曲,像《太子赞》、《孝子董永》、《季布歌》,都是很粗豪的东西。用白话写的小说,像《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之流,也足以供我们以最重要的最早的国语文学的研究资料。”最重要的当然是变文了,郑先生说:“变文的重复出现于世,关系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极大。这是五六百年来,潜伏在草野间而具有莫大的势力和影响的宝卷、弹词、鼓词一类文体的祖先。”以下谈及宝卷等俗文学文体,都以变文为其源头。如说:“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到底什么时候才把变文之名易为宝卷,则文献无征,不易考知。惟宋初尝严禁宗教,并禁及和尚们讲唱变文,则易名改辙,当在其时。”“弹词也是源出于变文的。不过不带着任何宗教的臭味而已;他们是叙述人间社会的活动的。其体裁却和变文非常相同。”“鼓词或‘鼓儿词’的亲祖,也是变文。她和弹词,区别之点并不多,惟鼓词流行于北方,江南罕见之;而弹词南北皆见风行。”“‘诸宫调’也是叙事歌曲的一个体裁,显然也是从变文衍变出来的。其和变文、宝卷等等大不同之点,在于其唱文的一部分,并不是袭用七言的句法,而是采用到流行于宋、金、元的各种曲调以组成。”[②]正是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学人们对已有的材料的观念,也便联带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文学史上重大问题的看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1936年,郑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陆续出版,第五册收录了《王梵志诗一卷》,第六册收录了《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第九册收录了《八相变文》,第十册收录了《大目毽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序》、《目连变文第二种》、《目连变文第三种》,第十一册收录了《维摩诘变文第二十卷》、《维摩诘变文持世菩萨第二》、《维摩诘经变文“文殊问疾第一卷”》,第十二册收录了《王昭君变文》、《舜子于孝变文》。这些材料,一部分是国内已经出版了的,一部分则是他从伦敦和巴黎抄回来的,还有一些是国内收藏而刚刚发现的,几乎包括了当时发现的敦煌俗文学的全部。郑先生还给他收录的这些敦煌俗文学作品分别写了跋语,就作品内容、抄卷情况、文学价值作了说明。不久,他又把这些敦煌文学资料汇集起来,编成《敦煌俗文学参考资料》,有燕京大学、暨南大学油印本。
郑振铎先生是一个有着高度学术眼光的学者,在俗文学研究领域,他更是具有全局的眼光。他总是把敦煌发现的俗文学资料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去判断其价值,这是郑先生的高明之处。1929年,郑先生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上发表了《敦煌的俗文学》(后收入作者《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为第三篇第三章,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年),在第4期上发表了《词的起源》(后收入作者《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为第三篇第一章)。这是两篇都很重要,尤其是《敦煌的俗文学》,在敦煌文学研究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它首倡“敦煌俗文学”的称号,充分肯定了敦煌俗文学的文学史意义,并对敦煌俗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分类研讨,通篇论文闪耀着理论的光芒。
关于《词的起源》,郑先生通过敦煌出土的曲子词,对传统“词为诗馀”(朱熹的“泛声说”,沈括的“和声说”,方成培的“散声说”)的说法提出了挑战,认为《旧唐书·音乐志》的说法是对的:“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这里的“胡夷之曲”和“里巷之曲”,便是词的两大来源。后来讨论词的起源的文章,在诸多细节问题上细致深入多了,但大致未能超出郑先生的范围。
《敦煌的俗文学》更是一篇结构宏伟、内容丰赡的伟著,论述了敦煌俗文学的很多问题,真知灼见,时见笔端。如敦煌俗文学的文学史价值,敦煌俗文学的分类,俗文学的体制、作者、时代等。这些问题在他后来的诸多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但有些观点在后来的论著中有所改变,有必要在此指出来。比如“俗文”和“变文”之分,这是郑先生早期力主分开的。所谓“俗文”其实就是讲经文,它是先引经文,然后再敷衍故事;而变文则是直接讲述故事。由于当时所见材料有限,加之郑先生对“俗文”内部结构的分析还欠细致,他的论述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讲经文”“变文”还有区别。所以后来他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认为区分“俗文”和“变文”是错误的,便放弃了“俗文”这种文体,“原来在‘变文’外,这种新文体,实在并无其他名称,正如‘变相’之没有第二种名称一样”[③]。
郑振铎先生《中国文学史》“中世卷”出版后,“古代卷”和“近代卷”并没有完成。1932年,北京朴社出版部出版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是一部迄至那个时候为止篇幅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其史料的充分受到鲁迅、浦江清、赵景深等学者普遍关注[④]。在该书的《自序》中,郑先生说他之所以要编文学史,乃是“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它们共同缺失的,正是俗文学这一大宗。而在郑振铎看来,这样的缺失,是像英国文学史缺了莎士比亚与狄更司、意大利文学史缺了但丁与鲍卡契奥(薄伽丘)一样难以原谅的。在《例言》中又说:“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在本书的《绪论》里,郑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史除了“诗歌、散文二大文体之外,更要包罗着文学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戏剧、小说与‘变文’(即后来的弹词、宝卷)”。在本书的《中世文学》卷,有《五代文学》一节中,论及敦煌曲子词和《叹五更》、《孟姜女》、《十二时》等民间杂曲。而专列《变文的出现》一章,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敦煌变文的发现、来源、流传、消亡及体制特征。本书讨论变文的体制是同汉译佛经的比较中进行的,因为变文的体制和一部分以韵散组合而成的佛经完全相同。汉译佛经的“偈言”(即韵文部分)都是五言诗,而变文歌唱的一部分,则采用了唐代流行的歌体或和尚们流行的唱文,而有了五言、六言、三三言、七言及三七合成的十言等句子形式。而变文的散文部分,郑先生的分析更有启发性:唐代的通俗文乃是骈俪文,而“散文”(古文)则是高雅的文士文学。从唐初张文成的《游仙窟》到敦煌变文的散说部分,都是插入了大量的骈俪文。这当然是因为骈俪文流传数百年,民间熟悉了骈俪的文体,时代风气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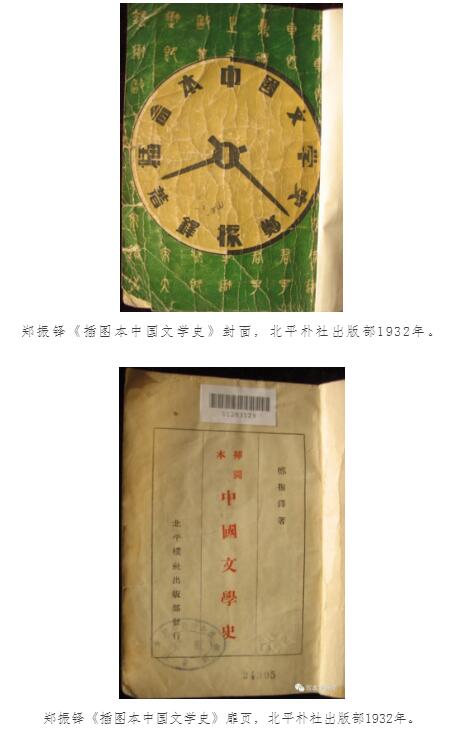
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郑先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长期被正统文人所忽视的俗文学、民间文学,乃是文学发展的“原动力”,他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到了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中,郑先生把这种“原动力”学说,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文学“中心”说。其基本思路是:中国传统向来只尊崇诗文,而世界各国文学史无不以小说、戏剧以及诗歌为中心,所以,那些历来不被重视的内容丰富的俗文学,不但是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又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原动力”,许多正统文学的文体,都是由俗文学发展而来,因此,“‘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⑤]。
《中国俗文学史》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郑振铎从中国文学史的总体发展角度来审视俗文学的重要作用与地位,论述俗文学与正统文学的辩证关系,揭示俗文学的六大特质和类别,指出了它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传承性等特点。其中有《唐代的民间歌赋》(第五章)《变文》(第六章)两章论述敦煌俗文学,而这两章也是对敦煌通俗文学的分类。《唐代的民间歌赋》评价了王梵志的诗、曲子词、俚曲、长篇叙事诗(词文)和俗赋等,而对敦煌俗赋的评介尤其具有学术眼光。比如他把《茶酒论》和《齖新妇文》归入俗赋进行讨论,认为《茶酒论》这种争奇类的作品,“本是从《大言》《小言赋》发展来的,明人邓志谟却把这幼稚的文体廓大而成为二册三册的一种‘争奇’的专书了”[⑥]。《变文》一节用了很长的篇幅对当时已经发现的变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其中对变文的文体涵义、来源、分类、体制特点等的论述,对后来的变文研究启发很大。而对变文的文学史意义的论述更是为后来的变文研究者乐于引用:“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明确的回答。”但自从敦煌石室发现了变文以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馀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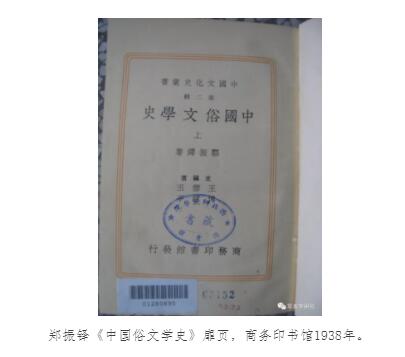
当然,郑先生一直坚信变文是从印度来的,他斩钉截铁地说:“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⑧]既然宋代以后作为中国文学“中心”的通俗文学,都是源于变文,那么印度文学就成了中国唐以后文学的源头了。这未免讲得绝对了些。我们知道,变文的韵文部分的句式、散文部分的形式,都大量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学之中;变文韵散交错的结构,也能在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找到同样的类型;变文按图讲诵的形式,也可以在先秦两汉的史料中找到[⑨]。所以,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变文是在中国固有的文艺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借用这种形式诱导听众,宣传教义,更是借用这种长期存在于中国民间而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而不是搬用全新的、不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外国文艺形式。当然,从另一角度说,正是佛教化俗的这种变文形式,促使中国原有的讲唱艺术形式更加成熟,更加繁荣昌盛。
[①]《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郑振铎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399页。
[②]《郑振铎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468-488页。
[③]《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出版部1932年,591页。
[④]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见《鲁迅全集》书信集;浦江清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写的书讯,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8月1日,后收入《浦江清文史杂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赵景深《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载郑振铎编《我与文学》,上海书店,1934年。
[⑤]《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2页。
[⑥]《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175页。
[⑦]《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180-181页。
[⑧]《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191页。
[⑨]参见伏俊琏《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俗赋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134-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