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先生逝世60周年。在先生诞辰110周年、120周年的时候,我们文学所以及国家图书馆联合开了好几次会议,今年刚刚开过一个纪念会,下午故宫还有一个纪念会,会议很多。这说明郑振铎先生虽然离开我们整整六十年,但是我们仍然念念不忘。念念不忘的原因,从我个人来讲,他首先是一个百年不遇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是那一代学者中最优秀的代表、最杰出的典范。从我们单位来讲,他是我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第一任所长,同时也是考古研究所的所长,不久还兼任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作为一个学者,能够跨界、跨行做出这么多贡献,是十分罕见的。
我在我们今年《文学评论》的第六期专门组织了一组文章,从各个方面撰文纪念郑振铎先生。从文学专业的角度,郑先生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有两个,第一就是文学的理想,第二是文学的贡献。
我主要谈谈郑振铎先生的文学理想。第一,他认为文学是永恒的。他多次在文章中说帝王将相、凯撒大帝、拿破仑,他们留下的只是鲜血,只有文学给人留下的是温暖,是永恒的记忆,是真善美。这是郑先生对文学崇高的评价,历史多少次证明这个评价是一个最平凡的真理。
第二,文学是世界的。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文学大纲》等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编纂、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而且在他的视野中,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的理想和梦想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文学介绍到全世界,把世界的文学介绍给中国,把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这些年他一直在做这些工作,包括1953年成立文学所的时候,他在组织文学所的班子时,从各个方面请了一大批当时第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古今中外的第一流的专家。这是我觉得郑先生第二个特别让我们难忘的文学理想。

第三,他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是社会的。他在文学研究社成立时就谈到这么一个主张:叫大众的文学。何为大众的文学?大众的文学就是为大众创作、为大众服务,同理,研究也要为大众服务。这个观点从他二十几岁,一直到他的晚年,一直坚持这种主张。所以他在组织文学所工作的时候,他心中就规划了几套班子:第一个,成立组织编写大规模的世界文学研究丛书,包括翻译、研究;第二个,就是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典籍的丛书,包括《古本戏曲丛刊》,我们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终于马上要把郑先生60年前的遗愿完成了。明年,在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古本戏曲丛刊》画一个句号,他生前最后一篇文字就是《古本戏曲丛刊》第四期的序言,第二天上飞机,然后就再没有回来,这是他一生的梦想。我们到明年初要出版第八集,整个丛刊一共收录一千种典籍。这应该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专题古籍整理项目。要论规模之大,我想现在各省各种影印项目我们比不了。但是这么大规模的专题古籍整理项目,郑先生的《古本戏曲丛刊》是第一部。另外,郑先生还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把《古本小说丛刊》也做好,我们文学所和中华书局合作也完成了这个遗愿,郑先生生前设想的那些世界文学的名著,古典戏曲丛刊的译著等等也都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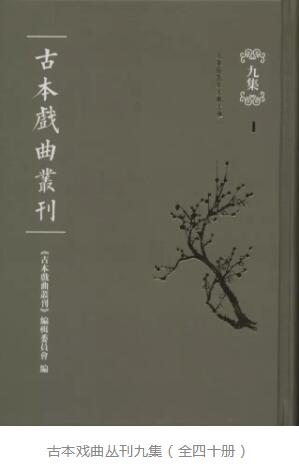
郑先生还有一个愿望,他认为文学是大众的、文学研究要为大众服务,所以当时我们文学所成立的时候,按照郑先生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请这些专家编一套能够给全中国人民看的一套读本。事实上今天我们文学所的老一代学者,包括钱钟书、孙楷第、余冠英等等这些在业内如雷贯耳,在社会上能够被社会广泛认知的学者,正是因为他们编了一系列的读本。这些读本注释经典,注释本的本身也已经成为60年来的经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迪。
我在第六期《文学评论》中发表文章,在谈到郑振铎先生的理想和学术研究实践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说郑先生本人最初只是想当一个学问家,他说他自己不愿意参会,不愿意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有一句话,他说,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当人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放下他自己手头的工作,叫他的那些老朋友出来为国家工作。他要舍去小我,要为国家的大我而服务。
我想郑先生最不可企及的不仅仅是文学理想,不仅仅是文学实践,更重要的是他的境界。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刘跃进
编辑/赵洪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