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中旬,李军兄即告诉我,沈燮元先生会在中秋节那一天由宁返苏,他希望与我见面。这几年,燮翁和我都感到年龄逐年增大,老朋友间见面实非易事,故只要燮翁在苏州,我们就一定要选个地方聊聊,而居中联络者就是李军兄。所以,国庆前的一天,我们又如约相聚在苏州博物馆的古籍图书馆里。

版本目录学家,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沈燮元先生
刚坐下,还没寒暄几句,燮翁就递过来一张纸,只说了三个字:“你看看。”原来是老先生和北京国图出版社合作,拟出版自己的文集,纸上是他手抄的目录。他要我拍下图片,让我为他的集子写篇序。他下的通牒是:“你给丁瑜的《延年集》写了序,我的书你能不写吗?”
我和燮翁是忘年之交,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就认识了,之间的互动,都是因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起。一九七七年秋,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图书馆专家学者为即将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起草了“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表”三个文件。次年的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八日,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全国会议在南京举行,而我们都参会并发表了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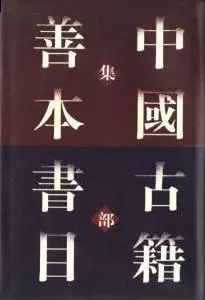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近百年来编得最好的一部联合目录,刚进入八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并不宽裕,物资仍然匮乏,但是编委会的工作始终有条不紊地奋力迈进。我还记得,那时我们每天在分编室里接触的是八百多个图书馆上报的卡片,面对各种不合常理的著录方式,也只能凭借过去的经验去辨识卡片上的著录有无错误。燮翁和我们私下里调侃说:我们这些人成天都和卡片打交道,我们都成了片(骗)子手了。当然,也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眼界才变得更为开阔,分辨及鉴定能力也相应提高许多。很多青年同事在经过这样的训练后,业务上也奠定了基础。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七年,编委会曾借上海图书馆的二〇六室,作为经部、史部复审、定稿的工作室,编委会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潘天祯、顾问潘景郑,与燮翁、任光亮、我等聚于一室。能和当时国内最好的版本目录学家一起工作,是我们几人的缘份。当年参加编委会汇编、复审、定稿的人员已大半凋零,如今仅存燮翁、丁瑜、任光亮、我四人了。燮翁是自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无论在南京、上海、还是在北京,他都坚决服从编委会的安排,从不讨价还价,认真做事,克尽厥职,功成不居,为《善本书目》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燮翁为了工作,四海为家,毫无怨言。我以为他参与编委会工作的十余年,是他数十年图书馆生涯中意最浓、色最灿、义最重的一段经历。
燮翁的版本鉴定能力很强,顾廷龙先生曾戏赠他一顶“派出所所长”的桂冠。一九八〇年代,我们在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工作期间,有一次同去北京某图书馆看一些有问题的版本图书时,编委会的何金元(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英年早逝)委托燮翁顺便也审看一下该馆藏的明正德刻本《中吴纪闻》。那是因为何金元在审阅此书卡片时,发现卡片上写有“据宋本校及清黄丕烈校”,并有李盛铎跋。他觉得“黄丕烈校”有疑问,曾请教过同在编委会工作的该大学馆某先生,某先生说没问题。但何金元不放心,就请燮翁和我去看一下黄跋的真伪。燮翁是研究黄丕烈的专家,当时已从事黄跋的搜集整理,所以他对“黄体”太熟悉了。果不其然,书刚一打开,他就一眼定“乾坤”。黄跋的字有些形似,但没有黄丕烈的韵味,那当然是后人摹写,而非黄氏手书。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虽收入此书,但删去有黄跋之语。那天我们还看了该馆一种明抄本,也有黄丕烈校并跋,纸较新,字迹是比黄丕烈还黄丕烈,又是书估作伪的小伎俩(后因抄本不旧,又有伪黄跋,删去不入目)。又如原作元泰定刻本的《广韵》,由杨守敬自日本购回,每页均裱糊,装钉形式悉日人所为,实为日本所刻,非中国刻本,亦不入目,此类例子尚有不少,不再赘述。
除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外,燮翁一生对文献学的贡献,自然莫过于对黄丕烈的研究。我总以为被誉为“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的黄丕烈,实在是藏书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只要读读他的《藏书题跋记》,你就可以知道这位佞宋刻,嗜旧钞,为先贤存古留真的学者是何等的“痴”,别样的“淫”。至于其精校勘, 析疑义,详考辩,求古籍尽善尽美,完全凸显了乾嘉学人的风貌,至今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交口称赞。

黄丕烈像
近百年余来,黄跋先后经几代学者多方搜集、汇编成书,先是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再由江标辑《续录》,其后缪荃孙、章钰、吴昌绶又集南北各藏书家所见,辑成《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补遗》一卷、《刻书题识》一卷。之后,王大隆续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再续录》三卷《杂著》一卷,极大地丰富并详尽地记述古书版本、校勘内容和收藏源流,这对于研究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学者们,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燮翁以一人之力,四十余年如一日,每天都和黄氏进行时空“对话”,说他是黄氏的异代知已,那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要做黄丕烈的年谱、重新辑佚荛圃题跋。但是,燮翁和黄氏都是苏州人,不能说没有一点乡邦之情,更或许是他被黄氏的藏书魅力所诱惑。在前人的基础上,燮翁费尽心机,多方辍拾,矻矻不倦,终于从中外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等处,新发现他人未见之黄跋数十则,同时还纠正了旧辑本的不少讹误。因此,到目前为止,燮翁所辑的《士礼居题跋》应是最全、最好、最重要的黄跋本子,不久之后,该书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此外,燮翁又重新辑录黄氏诗文,编纂黄氏年谱,皆大有裨益于文献学研究者。
一九九〇年,八七高龄的顾廷龙先生曾为燮翁写过一付对联,句云:“复翁异代逢知己,中垒钩玄喜后生。”这是对燮翁在版本目录学、黄丕烈研究两方面恰如其分的评价。他整理的《士礼居集》分题跋、诗文两部分,问世有期,令人欣喜。此外,燮翁数十年所作文章,汇编成此文集,反映了他一生治学的概貌。文集所收,计文八篇,跋五篇,序五篇,以及年谱一种、方志目录一种,凡二十篇,十余万字。尽管数量、篇幅并不巨大,细读之下,我才知大手笔作文,轻易不肯动手,一落笔必言之有物,有理有据。从小文章中,可窥见燮翁考证工夫之细密。如《嵇康集佚名题跋姓氏考辨》,纠正之前两位学者考证的失误,并得出“凡从事版本鉴定,无非都要从行格、避讳、刻工、刀法、纸张多方面去考虑,但我觉得书法的比对,印章的辨别,也可以作为鉴定版本的不二选项”的结论。
版本目录学是一门从实践中来的学问,只有在图书馆编目及采购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才能练就一双鉴定版本的慧眼。早在五十年代初期,二十余岁的他,就在赵万里先生的指导下,为北京图书馆购书,先后买到《韩诗外传》(明万历刻广汉魏丛书本,清卢文弨批校)、《南唐近事》(清嘉庆二十年吴翌凤抄本)、《资世通训》(明刻本)、《梅妃传》(清吴氏古欢堂抄本)、《杨太真外传》(清吴氏古欢堂抄本)、《长恩阁丛书十四种》(清末傅氏长恩阁抄本,清傅以礼校)等。一九五五年以后,他调入南京图书馆,退休前曾任古籍部副主任,但没架子,不钻营取巧,也没有那种羡慕荣华之心,而是把心思都用在业务工作上,数十年间为南图征集到不少重要善本。其中如北宋刻《温室洗浴众僧经》一卷、辽代重熙四年(一〇三五)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一卷等,已成为国宝级藏品。

而今耄耋之年的燮翁,三十余年里退而不休,坚持每天风雨无阻地去南图古籍部,不仅日日伏于几案,潜心典籍,还不时为读者排忧解难,指点迷津,为他人作嫁衣裳。我的《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一百二十万字,在出版前,也曾请燮翁全部校读一过,对此我非常感谢他。无论我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与我的通信,我全部都保存了下来,厚厚一迭,居然也有四五十通之多。
最令我感动的是,去年五月我们在李军兄的引导下,去祭拜顾廷龙先生墓,如果说我跪拜先师是天经地义之礼,但燮翁也要跪拜,我说:“您就不要跪了,鞠三个躬吧。”他说:“不行,顾老对我有恩,提携过我,我是一定要跪拜的。”一位九四老人,腿脚不便,平时行动缓慢,走路都谨慎小心,却坚持要做如此这般“大动作”。当时我侍立在旁,礼毕,赶紧扶他慢慢起立,只见他喘个不停。今年五月,我们又连袂去苏州十梓街看复泉山馆(顾廷龙故居),还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呢。
说到底,燮翁是一位平凡的读书人,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业余爱好无他,就是喜欢书。我看到他在苏州居所的书房,各式的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的图书,以及相关的参考书、工具书,排放整齐,即使小部分的港台出版物,他也透过相应的渠道多方访得,而他在南京住处,图书也是堆积如山。除了书之外,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不知是否还有嗜酒若燮翁者?还记得三十年前,同道们互传燮翁喜酒,但不能多饮,每次一小杯,多则要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长青。这是燮翁认可之说,直到今日,他仍保持旧日习惯,但并不贪杯,或许小酒也是他的长寿秘诀之一!这样一位老人,思想上却并不僵化陈旧,他也领略一些社会上的娱乐八卦,不时关心科技领域中的新成果,套用一句时髦的话,他也在除旧布新,“与时俱进”。
燮翁高龄,今年九十有五,已踰鲐背之年,更难得是他康健如昔,不时往来于苏、宁两地。我不由想起“九五之尊”这个词,“九五”旧指帝王之尊,位高而不傲,有谦和之德。以燮翁目前在图书馆界中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地位,是当仁不让的老法师级人物,无人可出其上,其阅历资之深,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似乎也德配“九五”之词了。《礼记?曲礼》云:“百年曰期颐。”元人陈澔释云:“人寿以百年为期,故曰期;饮食起居动人无不待于养,故曰颐。”很多见过燮翁的朋友,都为老人的健康表现出欣羡之情。我亦以为,待到山花烂漫时,老人期颐之年,约上一班忘年之交,好好作一次畅怀痛饮。
燮翁嘱我为他的集子作序,实在荣幸之至。回顾四十多年的交往,拉杂写上一些感想,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于上海
(此篇文章为《沈燮元文集》序言,经作者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