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7-02-15
作者:刘晓立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即将走过十周年之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启动摄制纪录片《古籍今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纪行》,该片是以视频为载体对我国近十年古籍保护事业的简要回顾,同时也是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进入“十三五”期间的展望。
纪录片《古籍今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年纪行》由文化学者、纪录片制作人葛芸生领衔,日前已经采访了百余位专家学者与奉献在一线的古籍保护工作者,走进十省区数十处古籍收藏保护单位,积累了200个小时的真实影像。
对于葛老来说,这一切,不只是为了做一个节目,毕竟古籍保护的资源采集远胜于单一作品,保护比制作更为重要。他说:“走访时我更企盼各地能重视古籍保护全程‘进行时’的影像积累,它将成为古籍‘活起来’的、第一手的、不可再生的、兼备存储与传播双重持续功能的宝贵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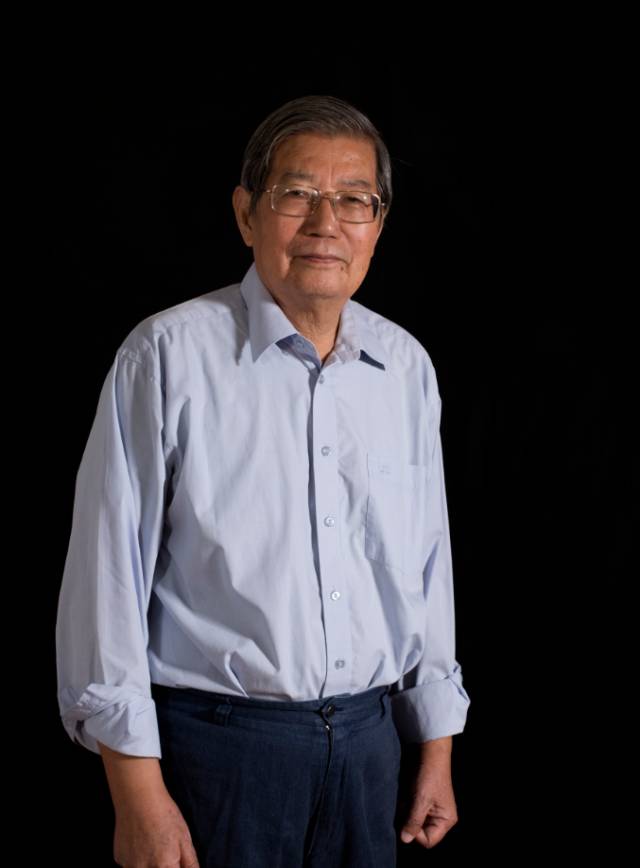
文化学者、纪录片制作人葛芸生
藏书报:做这个纪录片,要深入其中,让专家学者畅谈难题和心声,您有什么诀窍吗?
葛芸生:如果从新闻工作的角度,采访需要提前做选题和提纲,但实际上,我从来不喜欢采访时拿着提纲一条条地去问答,因为我要对方说的并不是我设计的主题,而是他真正想要说的。有一次,我在上海采访一位资深专家,才说了一句话,即古籍保护归根结底要做好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的保护,他就滔滔不绝地和我聊了起来,话题中不乏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尽管他今天说的话,在我的节目里只有几十秒钟,但我并没有打断他,而是专注地聆听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以及有困惑的话语。严格来说,我以聊天的方式有违采访常规,但无论权威还是基层员工,给予我的就是古籍保护有苦有乐、有血有肉的实感,令我为之流泪、为之欢欣。
古籍保护归根结底是对
人
的保护
藏书报:为什么说古籍保护的关键是对从事这项事业的人的保护?
葛芸生:举个例子吧。我去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采访,在那里不仅见到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院长肖惠华,还跟几个毕摩先生有了一番交流。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他们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念经、司祭、行医、占卜等;从文化传承上他们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包含宗教、哲学、伦理、工艺、礼俗等典籍。

水族先生译注经书
在贵州,水族称神职人员为先生。水族先生跟毕摩一样,临终前如没有合适的继承人,就会拿经书殉葬,所以,具有古籍资质的经书存量有限。目前经抢救,有的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的在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但在申报时必须把经书翻译出来,让公众知道这些经书的意义和价值。我在荔波遇上五六位水族先生正在做经书翻译,这些先生此前被当作封建余孽,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如今出来当翻译,并不计较钱的多少,而是要给本民族文化留个根。他们说,经书上的水族文字,往往一个字会有多个形、音、义。几位先生一起翻译,不同意见的争议不绝于耳。我在现场受到启发,倘若把他们的争论全部录下来,其价值将历久弥新,有可能是绝响。因为,上一代先生在口耳相传时,经书上许多内容仅仅以文字为表意符号,并不是精准的记述。所以一位先生他走了,他的东西就没人能懂了。
就我所知,我国有19个少数民族是有文字的,但是能够阅读和理解少数民族文献的人现在少之又少,古籍保护面临的难题,并不在藏量多不多,而是要重点保护那些能读懂的人,其中首先是那些先生和毕摩。
藏书报:少数民族文献是不是需要特别保护?
葛芸生:是的。保护那些记载着各民族独自语言、文字的古籍,就是在保护各民族的多样性。民族平等是不论人口多寡的,更何况少数民族的文献体量一般不大,传承条件差,人才稀缺,现存古籍还有需要靠毕摩等神职人员的释读才能弄清楚内涵。正如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水族文献专家潘朝霖痛心疾首地和我讲:这些持有文献的神职先生要是一个人不在了,倒掉的就是一座图书馆;图书馆倒了可以重建,人走掉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
汉文古籍在十年普查登记中有三百多件新发现。其中大量是从原本收藏的库房里找到的,似花开二度,似遗珠落盘。相对来说,少数民族文献原先收藏不足,散在民间的居多,存放环境不利,如果再不抢救,可能就没了。接下来,少数民族文献的保护就像精准“扶贫”一样,应该花大力气去抢救与保护。不然的话,少数民族的文化变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藏书要有“三
善
”
藏书报:作为藏于民间的古籍,您认为应如何保护?
葛芸生:按照古籍属于“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不管公藏、私藏,都应该能为所有人所用。很多前辈藏书家都纷纷把个人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如郑振铎、周叔弢、顾廷龙、赵万里等先生,他们藏书不是为了个人增加财富,而是以藏书来服务国家和民族的。
我在苏州采访了一位古旧书店的老行尊江澄波先生,现在90多岁了,一辈子与古籍打交道。他的弟子有的是拍卖公司的老总,想从他那里拿点古籍去竞拍,他一件都不给。面对价值连城的“过云楼”原藏量75%的善本典籍,他却无偿地推荐给南京图书馆收藏,自己靠微薄的养老金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他最不愿意看到古籍的散失亡佚。

古籍版本专家、江苏文学山房主人江澄波接受葛老的采访
我在香港两次拜访收藏印谱的松荫轩主人林章松先生,他藏有一千七八百部印谱。著名版本学家沈津用两句话介绍林先生:您要用他的书,一个字“请”;您想拍几张照片,两个字“请便”。收藏家韦力的评价则是:“我叹服林先生的印谱,收藏从质量上讲已经很高;从数量上讲,更是中国第一。”令我最感动的是,有一半印谱林先生自己完成了编目与撰写提要;他的习惯是只藏不售,但始终坚持无偿服务于公众。他长年一丝不苟地利用博客,连续以数百万字的专文和海量图像,公示自藏的印谱。

沈燮元老先生向葛老讲述古籍
个人藏书家愿意不愿意捐献,诚然是自己的事,但我一直认为:收藏要有“三善”,即善心、善藏、善用。人生苦短,给书找到一个最佳的安置场所应被视为一种功德。
古籍保护可在
五
方面继续提升
藏书报:看了这么多,访了那么多人,您认为古籍保护工作还有哪些可提升空间呢?
葛芸生:综合受访者给我的教诲,目前粗浅的领会是,接下来古籍保护要在国家关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顶层设计下,注重从科学化、国际化、数字化、学术化、产业化五个方面,努力提升。
科学化,是指搭建古籍与当代科学并驾齐驱的通道。时代在进步,古籍保护不能停留在手工行业阶段,必须将现代科学融入其中。在这方面,我认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做得非常好,他们将古籍保护提升到跨学科融合的高层次,去年又有6位分别来自海内外从事生物、化学、物理、材料等多学科的博士与博士后加盟古籍保护研究院,同时又聚集了复旦校内的科学院院士、教授,一起攻克古籍保护领域的难关,解决“短板”。为此,启动的古籍用纸、用墨等材料的项目,即获得广州市前市长陈建华的首肯与研发费用一千万元,由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同研制解决“纸寿千年”难题。他希望未来再印《广州大典》时,能用上寿命更长、科技达标的优质纸。而这样的科学研究,必须要有先进机器、尖端人才,且进行一次又一次较长时间的科学实验。我在现场有幸见到首次检测的样品纸,并聆听到中科院院士、高分子和材料学家杨玉良先生的评点。接下来,人工试造的纸还有待对野生原料如草根、树皮的进一步筛选和种植养育的过程,才可能批量生产。在科学引领下,从纸张原料的种养基地,到古籍用材的科学检测、古籍修复与存储涉及到的大量设备与材质、古籍保护人员的培训与学科建设、古籍数字化与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都将需要花大力气来做。
古籍保护走向国际化,这是我走访中颇受触动的一个话题。通过近些年对海外存藏中华古籍的调查,已大体清楚海外哪些国家馆藏着多少中文古籍。出乎意料的不只是数量之众,而是如此多的中文古籍都在“睡大觉”,二三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也不见动一下。主要原因在于海外缺人手,缺少知晓中华古籍的人。这些海外古籍隔断了它原有的根脉联系,但它们确确实实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需要交流。我在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听到很多很好的中外交流的经验。显然,这种交流不仅停留在海外古籍数字化及影印出版上,更需要加强人才之间的交流。目前,国内有一批称职的古籍保护人才,他们可以“走出去”,前往所需国家进行中文古籍的修复与编目,同时也可以把海外学者“请进来”,举办国际论坛,吸收国外先进的古籍保护科技成果。
古籍保护必须加强数字化进程,已属共识。我感到数字化的路还很长,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尽管,扫描录入是最基础的一步,但如何让千千万万人平等享用数字化的成果,才是更为困难的关键一步。目前数字化还未能真正实现畅通无阻,搜索问题是需要迫切解决的。有人批评一些上传数据有误,这类失误应尽量避免的,然而网络本身包含有纠错功能,所有人都可对某个信息提出不同意见,既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学术氛围,也促进“小众”的古籍保护得到“大众”的参与。数字化本身一方面便利了读者阅览,另一方面也帮助了古籍管理研究者,是一项令双方受益的工程。
无论在图书馆,还是在藏书与读者相对集中的高校,古籍保护如何迈向学术化之路日益引发关注。鉴于读者选择性需求的强化和阅读方式的跳转,古籍阅览室如何适应呢?古籍服务人员的学术水平,一定程度会制约提供服务的质量。故不能仅仅把古籍保护当做简单的职业,而是要视为一门科学。可喜的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与几所高校进行古籍保护学科的筹建,从培养专业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着手,逐步使古籍保护成为专门学科,培养目前从业的和更多未来从业的优秀人才。
资金缺乏,是受访者最不愿启口跟我说的话题。200多天所见所闻,多次引起我到古籍保护要不要、能不能尝试产业化的思考。平时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感叹,我们少建一座大厦、少修几公里高速铁路,省下的钱用在古籍保护这块沃土上,就能做出很多“改善土质”“花开二度”“百年树人”的功德善举。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国家倡导的文化创意产业,正为古籍保护的产业化奏响了序曲。
余生做
好
一件事
藏书报:对您来说,做“古籍保护纪录片”意味着什么?
葛芸生:21世纪初,我给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费孝通老先生做了一部纪录片。费老亲切地跟我说:“我身边只剩十块钱了,我要好好想一想买一件什么东西?”当时我没能领会,心想费老说得不会是钱吧。稍后才意识到费老的言外之意是,要珍惜余生去做一件有益国计民生的事情。这就是费老后来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水资源的调查与治理”项目。
我在云南贵州走访时,先后听到多起费老关注与抢救少数民族古籍的感人事迹,给我又一次强烈触动。我也七十有五了,身上也不清楚还剩几块钱。我要牢记费老的教诲,余生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倘若有缘的话可能就是古籍保护了。
前年我发起一个“古籍流辉”志愿者群,希望能以镜头和行知,将自己在亲近古籍中的点滴感受,传递给更多的人,与更多的人一起从古籍中共享智慧,滋养生命。
转载自《藏书报》2017年2月13日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