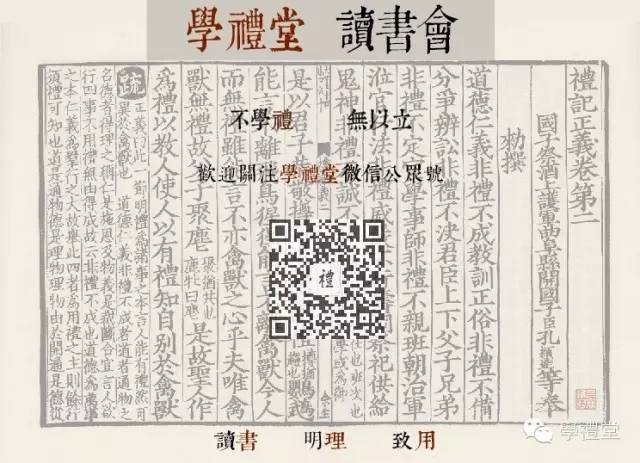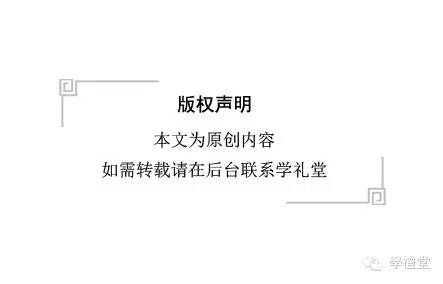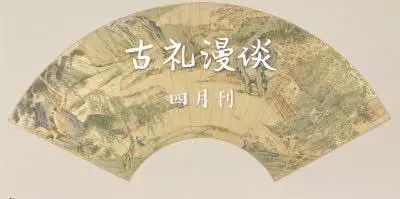
影印敖继公《仪礼集说》序
敖继公,字君善,元长乐(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寓居乌程(今浙江湖州),“筑一小楼,坐卧其中,冬不炉,夏不扇,日从事经史”,邃通经书,讲学授徒,湖州名士赵孟頫、倪渊、姚式、陈绎曾皆从其学,质问疑义。大德初年,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高克恭推荐于朝,授信州路儒学教授,未任而卒。敖氏深于《三礼》,尤善《周易》,常与钱选“讲明酬酢,咸诣理奥”,相传有《文集》二十卷,今传者惟《仪礼集说》十七卷(廖明飞《敖继公小考》)。
《仪礼》虽有郑《注》贾《疏》,然自唐开元以来,地位式微,“殆将废绝”。北宋王安石主持完成《三经新义》之后,《仪礼》被排除在“九经”之外,研读者甚少。南宋时期,朱熹因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乃集门人黄榦等以《仪礼》为主,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仪礼经传通解续》二十九卷,杨复重编《仪礼经传通解续祭礼》十四卷,编纂《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李如圭撰《仪礼集释》三十卷、《仪礼释宫》一卷,魏了翁编《仪礼要义》五十卷。及至元代,有马廷鸾《仪礼本经疏会》九卷、吴澄《重刊仪礼考注》十七卷、《仪礼逸经传》二卷、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汪克宽《经礼补逸》九卷等,敖氏《仪礼集说》最为有名。
敖氏《仪礼集说序》曰:
继公半生游学,晚读此书,沉潜既久,忽若有得。每一开卷,则心目之间如亲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与之揖让周旋于其间焉,盖有手之舞、足之蹈而不自知者。夫如是,则其无用、有用之说尚何足以蒂芥于胸中哉?呜呼!予之所玩者仅十七篇耳,而其意已若此。设使尽得三百、三千之条目而读之,又将何如耶?此书旧有郑康成注,然其间疵多而醇少,学者不察也。予今辄删其不合于经者而存其不谬者,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之以一得之见焉,因名曰“仪礼集说”。自知芜陋,固不敢以示知礼之君子。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亦未必无小补云尔。大德辛丑孟秋望日,长乐敖继公谨序。
大德辛丑是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仪礼集说》盖完成于此时。敖氏认为郑玄《仪礼注》“疵多而醇少”,故“删其不合于经者而存其不谬者”;若“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之以一得之见焉”,故名《仪礼集说》,自信于《仪礼》或有“小补云尔”。
《仪礼》十七篇,《仪礼集说》分为十七卷,每篇一卷。敖氏解释《仪礼》,每篇先大字录经文于右,次标“注曰”,摘录郑《注》,次以“继公谓”,申说补正;或于经文之左,直接注解;或偶引“马季长曰”“疏曰”“陈用之曰”“朱子曰”“李微之曰”“杨志仁曰”,摘录马融、贾公彦、陈祥道、朱熹、李心传、杨复等人注解,后以“继公谓”发表己见。每篇经文,划分章节,以“右某某”形式区别,如《士冠礼》之“右筮日”“右戒宾”之类。经文之下,偶尔摘录陆德明《仪礼释文》;部份卷末,有“正误”数条,勘正经文。细观此书,条理秩然,简明扼要,训释经注,时有新见。
《丧服》“小功章”曰:“从父姊妹孙适人者。”郑《注》曰:“从父姊妹,父之昆弟女。孙者,子之子。女孙在室,亦大功。”贾《疏》曰:“此谓从父姊妹在家大功,出适小功。不言出适,与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报之,故不辨在室及出嫁也。以女孙在室,与男孙同大功,故出适小功也。”敖氏《集说》卷十一曰:“从父姊妹孙适人者:三者适人,其服同。云‘适人’,则为女孙无嫌,故不必言女。”黄以周《礼书通故》第九曰:“敖继公云‘从父姊妹孙适人者’当连读,三者适人,其服同。以周案:‘张氏、蔡氏、程氏、胡氏并从敖说。从父姊妹适人者小功,则在室大功。故“大功”从父昆弟郑《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贾与郑违。’”黄以周赞同敖继公“从父姊妹孙适人者”连读之意见,并指出郑玄、贾公彦之非。
《燕礼·记》曰:“若与四方之宾燕,则公迎之于大门内,揖,让,升。宾为苟敬,席于阼阶之西,北面。”郑《注》曰:“苟,且也,假也。人臣不敢亵烦尊者,至此升堂而辞让,欲以臣礼燕,为恭敬也,于是席之,如献公之位。言苟敬者,宾实主国所宜敬也。”敖氏《集说》卷六不录郑玄注,解释曰:“苟,诚也,实也。苟敬者,国君于外臣所燕者之称号也。此燕主为宾而设,宾于是时虽不为正宾,而实为主君之所敬,故以宾为苟敬也。”《聘礼·记》曰:“燕则上介为宾,宾为苟敬。”郑《注》曰:“崇恩杀敬也。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敖氏曰:“苟敬,亦尊宾也。”凌廷堪《礼经释例》卷十三征引戴震之说,谓“苟”当作“茍”,与“苟且”字不同。《说文》曰:“茍,自急敕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急者,褊也;敕者,诫也。”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曰:“诸家说‘茍’为‘敬’之初文,是也。急敕,谓持身谨敬。云‘自急敕’,初义犹存。”郑玄认为,“苟”者,聊且粗略之意,“苟敬”者,杀敬、小敬也。敖氏解“苟”为“诚”“实”,“苟敬”者,尊宾也,主国国君宴请外国使臣之称号。敖氏之解,似优于郑《注》。清孙诒让《古籀拾遗》卷中《楚良臣余义钟》释铭文为“于茍敬哉”,“茍敬”连文,证明戴震之说“至确”,“茍敬”乃商、周古礼。杨向奎先生《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曰:“上述‘宾为苟敬’一段,实为古礼。关于‘苟敬’之‘苟’字解释,二三百年争论不决,训诂大家戴东原、王引之都参与争论。我本人则同意戴氏的说法,字从羊省。如此则于殷、周两代,戴氏说均可通行。由此亦可以断定《仪礼》来源尚古,非后人所可假托者。”
《士昏礼》曰:“妇入三月,然后祭行。”郑《注》曰:“入夫之室三月之后,于祭乃行,谓助祭也。”贾《疏》曰:“此据舅在无姑,或舅没姑老者。若舅在无姑,三月不须庙见,则助祭。此亦谓适妇,其庶妇无此事。”敖氏《集说》卷二曰:“入,入夫之室也。祭行,谓夫家之祭方行也。妇入三月,然后可以入庙。故夫家必至是乃举其家常祭,欲令妇得助祭而成妇之义也。凡舅姑之存若没,其礼皆然。”黄以周《礼书通故》第六曰:“盛世佐云:‘《特牲》《少牢礼》妇人助祭者,内宾宗妇皆与,此不专指适妇。’以周案:‘三月祭行之礼,统舅姑存歾、妇之适庶。敖、盛说是。’”此谓无论舅姑存歾,适妇、庶妇入夫家三月之后,方参与祭祀。
《士昏礼》:“匕俎从设。”郑《注》曰:“执匕者、执俎者,从鼎而入,设之。匕,所以别出牲体也。俎,所以载也。”贾《疏》曰:“《士丧礼》举鼎,右人以右手执匕,左人以左手执俎,举鼎人兼执匕俎者,丧礼略也。《公食》执匕俎之人,入加匕于鼎,陈俎于鼎南,其匕与载,皆举鼎者为之。”《士昏礼》有“陈三鼎于寝门外东方”,三鼎者,豚鼎、鱼鼎、腊鼎,郑《注》贾《疏》于此皆未言匕、俎之数,惟言盛俎之法,故敖氏《集说》卷二曰:“匕,所以出鼎实也。俎,所以载也。执匕俎者,从鼎入而设于其鼎之西也。设,谓设俎也。既设俎,则各加匕于其鼎,东枋,遂退此三匕。三俎从设,则是有司三人各兼执一匕一俎与!”黄以周《礼书通故》第六曰:“沈彤说:‘当有六俎六匕。云共牢者,谓夫妇各食其半,非谓止三俎而共之也。’以周案:‘经言夫馔举俎鱼腊言,妇馔不举者,明同牢亦同俎也。沈说无据。《少牢礼》匕皆加于鼎,东枋,为鼎西面,匕者在东便也。此鼎亦西面,匕者当亦在东,西面匕。贾《疏》谓南面匕,未是。宜从敖说。’”《昏义》曰:“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昏礼有三鼎,必有三匕三俎,故黄以周从敖氏之说。
《仪礼》十七篇,《既夕礼》是《士丧礼》之下篇,《有司彻》是《少牢馈食礼》之下篇,实则只有十五篇,除《士相见礼》《大射》《少牢馈食礼》等三篇外,其余十二篇皆有记文。《丧服》第十一篇,除经、记之外,且有传,与其他各篇均不相同。关于《丧服》篇经、传、记之关系,是《仪礼》研究之重要问题。敖氏《集说》卷十一曰:
他篇之有记者多矣,未有有传矣。有记而复有传者,惟此篇耳。先儒以传为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记明之,《汉·艺文志》言《礼经》之记,颜师古以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是也。而此传则不特释经文而已,亦有释记文者焉,则是作传者又在作记者之后明矣。今考传文,其发明礼意者固多,而其违悖经义者亦不少。然则此传亦岂必皆知礼者之所为乎?而先儒乃归之子夏,过矣。夫传者之于经、记,固不尽释之也。苟不尽释之,则必间引其文而释之也。夫如是,则其始也必自为一编而置于记后,盖不敢与经、记相杂也。后之儒者见其为经、记作传而别居一处,惮于寻求而欲从简便,故分散传文而移之于经、记每条之下焉(疑亦郑康成移之也)。此于义理虽无甚害,然使初学者读之,必将以其序为先后,反谓作经之后即有传,作传之后方有记,作记之后又有传,先后紊乱,转生迷惑,则亦未为得也。但其从来已久,世人皆无讥焉,故予亦不敢妄有厘正也。姑识于此,以俟后之君子云。
敖氏之意有五:一是《丧服》之传非子夏所作,作时在记之后;二是《丧服》之传既释经文,亦释记文;三是传文自为一编,附于经、记之后;四是为求阅读简便,疑郑玄分散传文于经文、记文之下;五是分散传文于经、记之后,使传、记之撰作时间紊乱,转生迷惑。
一九五九年发现武威《仪礼》简甲本、乙本各有《服传》一篇,是《丧服》“传”之单行本;丙本是《丧服》,包含经文、记文。陈梦家先生《武威汉简》一书认为:武威甲本系失传的庆普本,丙本《丧服》为西汉初(约当景武之世)相承的经、记本,甲、乙本《服传》则为昭宣之世出现的删定本,西汉初先有《丧服》的经,然后附以记,西汉中期经过对于经、记的删削而作“传”,分系于相当的经、记之下;东汉晚期的古文家,将删定的传文重新分属于全经全记本,遂成今日之郑《注》贾《疏》本。木简甲、乙本系西汉晚期之钞本,约成帝前后,其据之原本,约在昭宣之世;丙本竹简早于木简,乙本或早于甲本。敖氏认为《丧服》“传”单行,后分散于经、记之下的观点,被武威《仪礼》简所证明,可谓卓识。
正因如此,敖氏《仪礼集说》备受明、清学者重视。清《三礼》馆纂修《仪礼义疏》时,以敖氏《仪礼集说》为宗,《钦定仪礼义疏凡例》曰:“元儒敖继公《集说》,细心密理,抉择阐发,颇能得经之曲折。其偶驳正注疏,亦词气安和,兹编所采特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曰:
然于郑《注》之中录其所取而不攻驳所不取。无吹毛索垢、百计求胜之心。盖继公于礼所得颇深,其不合于旧说者,不过所见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矫激以争名。故与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随声佐斗者有不同也。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卷末各附《正误》,考辨字句颇详。知非徒骋虚词者。其《丧服传》一篇,以其兼释记文,知作于记后。又疑为郑康成散附经、记之下,而不敢移其旧第。又十三篇后之记,朱子《经传通解》皆割裂其语,分属经文各条之下。继公则谓“诸篇之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为两条而发者,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亦有于经义之外别见他礼者”,不敢移掇其文,失记者之意,自比于以“鲁南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卷末特为《后序》一篇记之。则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遗,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
敖氏《集说》于所不知,则曰“未闻”“未详”“不可强通”,故四库馆臣谓敖氏“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遗,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评价可谓公允。
敖氏乃一介书生,故《集说》疏谬之处,间亦有之,清儒钱大昕《潜研堂集》、褚寅亮《仪礼管见》、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皆有揭示,均可参看。
据廖明飞《敖继公〈仪礼集说〉版本小识》考证,《仪礼集说》十七卷版本有刻本和钞本两类,刻本有元刻本、《通志堂经解》本,钞本有《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四库全书》本、清钞本等,《通志堂经解》本、钞本皆源自于元刻本。元刻本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始刻于西湖书院,后书板归南京国子监,继续刷印,故元刻本有元刻元印、元刻明印本之区别。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日本东京静嘉堂各藏元刻元印本一部,分别是沈氏研易楼和陆氏皕宋楼旧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帙一部,存第十七卷,是内阁大库旧藏。元刻明印本今存六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两部,一是徐乃昌积学斋旧藏,一为莫伯骥五十万卷楼旧藏;中国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一部,是刘承干嘉业堂旧藏;中国台湾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一部,是张钧衡适园旧藏;天一阁博物馆收藏一部,缺第八卷;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一部,缺卷十三至十七。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一部清钞本,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蓝格,八册,是清代藏书家袁廷梼五砚楼故物,是常熟翁氏后人翁之熹捐赠。
清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二曰:
《仪礼》十七卷,题曰敖继公集说,元椠元印本。每页二十四行,每行十八字,经顶格,注低一格,版心有字数,间有刻工姓名。前大德辛丑自序,后有后序,十一卷后有识语。所采诸家注,郑《注》贾《疏》而外,朱子之说为多,此外惟马季长、陈用之、李微之数条而已。每卷后有“正误”数条,言所以去取之意,如后世校勘记之类,惟卷一、卷十一独无,与通志堂刻同,似以无所校正而然,非缺也。何义门不察,疑为缺而访求,误矣。卷十一末“大功二小功二”句下,《通志堂》本空四字,此本损破四字,以白纸补之,则通志堂所刊即以此为祖本矣。顾亭林《日知录》举监本脱误各条,此本皆不脱,则所据犹宋时善本也。
陆心源所言《仪礼集说》十七卷,即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之元刻元印本,惟有个别文字破损,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著录。
中国国家图书馆徐氏旧藏元刻明印本《仪礼集说》十七卷,已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此本每卷首行顶格题“仪礼卷第几”,次行题“敖继公集说”,《仪礼》篇名、经文顶格,“注曰”“朱子曰”“继公谓”等低一格。半页十二行,每行十八字,细黑口,对鱼尾,上鱼尾上记字数,下记书名、卷次、页数,下鱼尾下偶记刻工,有孙仁刊、汪惠、元、金等,左右双栏,二十四册。扉页题“元椠本仪礼集说十七卷,南陵徐氏积学斋藏书”一行,卷内钤盖“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朱文长印)、“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朱文长印)、“北京图书馆藏”(朱文方印)。徐乃昌(一八六九——一九四三),字积余,号随庵老人,安徽南陵人,近代著名藏书家,今藏北京市文物局之元刻明修本《十三经注疏》,乃徐氏旧藏。
将徐氏旧藏元刻明印本《仪礼集说》十七卷,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通志堂经解》本《仪礼集说》十七卷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有以下不同:一是此本卷末“正误”不全,除陆心源所言卷一、卷十一无“正误”外,卷十三、卷十五亦无“正误”;此本卷三“正误”两条、卷四“正误”一条、卷十七“正误”四条皆缺,《通志堂经解》本不缺。二是此本缺敖继公于大德辛丑仲秋望日《仪礼集说后序》,《通志堂经解》本有。三是此本有缺页,如卷九《公食大夫礼》缺第一页A面文字,卷十五《特牲馈食礼》缺第一、第二页文字。四是此本有断板破损,导致部份文字残缺漫漶,如卷十五第四十二页、卷十六第一至四页、第十五、十六页、第二七、二八页等。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监本二十一史》谓《仪礼·士昏礼》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五篇脱文合计四十六字,此本皆有,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和文物价值。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方便读者,可喜可贺!
首图出自故宫博物院藏仇英兰亭图扇页
微刊主编:子璋
文字编辑:越之 子昕
版式设计:子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