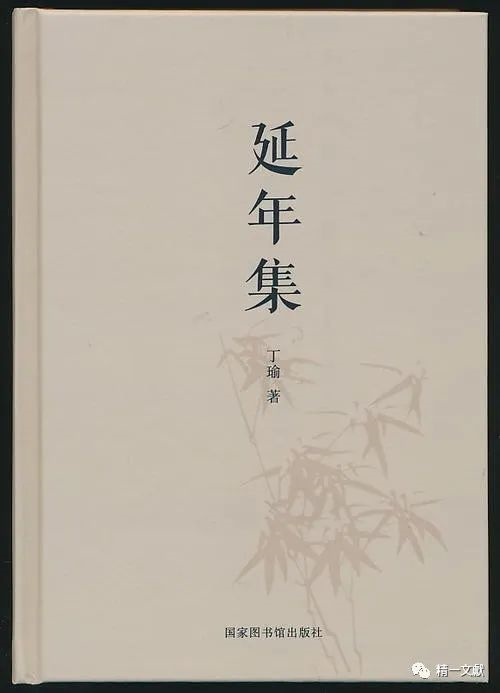
《延年集》 丁瑜先生著
丁瑜先生的文集,终于要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且期盼已久的事,也是国家图书馆策划的又一件有意义的事。
丁瑜先生,是河北高阳人,我国老一辈的版本目录学家。早在1968年,北京图书馆原善本组林小安先生到上海,我即知其大名。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0年5月,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从事版本目录学工作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为落实已故周恩来总理“要尽快地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遗愿,集中于北京香厂路国务院招待所一起工作时。我见到的丁瑜是一副慈眉善目、胖乎乎温文尔雅的“老干部”模样,五十四岁的他,头发已经有点斑白,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一双北京老布鞋。我总感到他风度翩翩,似乎“温良恭俭让”都被他占了,有意思的是,大家都尊称他为“丁公”。
丁公,今年高寿九十,是“九十年来留逸志、八千岁后又生春”的人物,是业界的前辈,二十三岁即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三十五岁时,从中文编目组长的职位调至善本组,在赵万里、冀淑英、陈恩惠三先生的指导下,习版本目录之学,这在当时,是领导有意要培养丁公,有点“接班人”的意思。如今,在我之前入行的几位先生都已是耄耋之年了,其中沈燮元先生九十有三、王贵忱先生八十有八。以丁公数十年阅历,加上他丰富的经验,注定成为德高望重的业内精英,也就是上海人口中被尊称为“老法师”的学者。
丁公是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对于古籍版本鉴定眼光独到。记得1979年在南昌举行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一次会上,某图书馆为配合会议,专门将馆藏的一些善本陈列,邀与会者鉴赏。其中有一部《大广益会玉篇》,题作“元刻本”。我以为有疑,于是有人请来丁公审定,他有如老吏断狱,直言此乃“日本刻本”。由此可见丁公版本经验之丰富、深厚。
1973年,丁公偕路工先生去苏州访书,所得颇丰,这在江澄波的《古刻名钞经眼录》多有载及。比如,明归昌世手稿本《假庵杂著》一卷和《记季父遗言遗事》一卷、清费云溪手抄本《青丘诗集撷华》八卷等,又尤以明黑格抄本《野客丛书》三十卷为最难得,盖此本为明弘治正德间黑格抄本,虽残存四册(卷一至十五),但字里行间及书眉上皆有校字,并有清黄丕烈跋。此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江氏得之于南浔张钧衡之孙,“后为北京图书馆丁瑜同志来苏收去,为此书目前传世之最古之本”。这里要说明的是,“文革”以后,很多图书馆恢复了古书采购,于是当时的北图委托江澄波,留意能否在江南地区,包括无锡、镇江、苏州,看看有没有民间收藏家在“文革”劫后遗下之书。江氏通过关系居然找到了不少,当然最后全部给了丁公。
七十年代末,丁公又和冀淑英先生一起,在南京觅得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梅花衲》一卷、《剪绡集》二卷。两书原亦为南浔张氏适园旧藏,“文革”中在苏州流散,为江氏所收。其时,北图已有翁同龢藏毛氏影宋抄本,但经过核对,两书行款字数不同,并且此本有用白粉涂抹校改错字之处,故其内容较翁藏本为佳。清孙从添《藏书纪要》云:“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划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故这两种书是近代藏家所重视的精品。
我以为,丁公最大的贡献在于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部大型工具书,共著录除台湾地区、香港特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寺庙等781个单位的藏书约6万种,13万部。在《书目》编委会中,除浙江图书馆二位,其他馆多是一位,而北京图书馆参加具体审订工作的有冀淑英、丁瑜及陈杏珍先生,上海图书馆则有顾廷龙、任光亮和我,南京图书馆有潘天祯、沈燮元及宫爱东先生。在编委会开始工作前,丁公就曾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版本鉴定及著录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古籍善本书著录浅说”的报告,为以后各省市图书馆古籍善本著录统一了思想。《书目》从编纂到出版,共费时十八年之久,当年编委会中完整经历了初审、复审、定稿的工作人员也仅为上述九位,如今尚健在者仅沈燮元、丁公、任光亮和我四人了。丁公在《书目》编纂过程中,老成持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笃行不倦。他和北京、南京的专家都克服了家庭中的困难,毅然以大局为重,在上海待了几个寒暑,终于完成了编纂任务。
这本集子里收录了丁公这些年来所写的各种文章。其中有关于簿录之学的介绍,或叙述一些重要版本古籍的来龙去脉,也有对前辈的回忆。他还用丙寅生、丁岳、丁令威的笔名写过多篇文章。我以为丁公最着力的,还是为原北图修复专家肖振棠的古籍装订修复工作进行系统整理而成的《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以及对清钱曾《读书敏求记》的校理。
我特别喜欢听丁公讲旧日在北图善本部经历的事,我也曾对丁公说:“您应该把在北图善本部跟赵万里、冀淑英先生接触的那些事情,包括看到的、听到的,或者赵先生对某些书的评价等等写出来,也可供后学者参考。”比如他曾回忆当年北图自香港得到湖南祁阳陈澄中藏书的事。陈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藏书家之一,他的藏书在1949年前后从上海转移到了香港,1964年,北图通过努力,由周恩来总理批示而得到了其中的部分。丁公把当时赵万里先生完成任务返京后,怎么去接站、清点、提验的过程,以及入库后,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北图做内部小型展览,一直到结束,那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因为只有他在场。我深切地感受到,版本目录学领域中的许多轶事、佳话、藏书故实,须靠当时经历人的回忆亲笔写出来、留下去,其他人是杜撰不了的。可惜的是,丁公因忙于其他事务而写得不多,很多事情将来可能就湮没了。
丁公能诗词,这是过去我所不知道的,他也从不在朋辈中说起。在中国图书馆学界、版本目录学领域,真正会作诗词的不多,我所知仅有上图的潘景郑先生和大连馆的张本义先生。我不会作诗,更不懂词,但知“诗言志”。《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打开丁公的《延年诗草》,映入眼帘的居然是数首新诗,且都作于40年代,正是丁公意气风发的大好时光,青年时的朝气,在诗中显露无遗。60年代又重拾旧好,不管是旧体诗词,或者是新诗,习得者各有所好,真可谓孤芳自赏,洁身自好,自得其乐。丁公曾将他的居所命名为“延年居”,所作诗也题作“延年”,或为他1940至2006年曾在德内大街延年胡同里度过了大半辈子生活,怀有美好的回忆而署的吧。
2011年前,我虽在大洋彼岸,但亦时与国内的良师益友保持联系,幸运的是,丁公诗中有几首涉及我。其中有二首的起因是2002年8月,拙著《翁方纲年谱》由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我将样书寄呈丁公指正。他读了我写的序文后,颇有感触,即掷下一信,有云:欣阅《年谱》全书,读史以知今,读传以知人,史传使人以悟世事,君之赐予我之帮助大矣。阅读之顷,率成七言二首,以寄友人,虽为七言八句,但非七律之韵,吾友当勿讥之。“羊年复始又开头,挚友情谊堪回眸。凌云壮志思鸿鹄,大洋彼岸率斗牛。书城挹翠添嘉话,著作等身胜二酉。点检琳琅诚如是,不朽名篇宏烨楼。”“来年花甲六十秋,春风哈佛更上楼。羡公文捷真良骥,笑我吟迟笨如牛。苏斋年谱拜读毕,订讹辨伪足消愁。明眼丹黄精神具,顾老门人第一流。”按诗中“书城挹翠”,是指我的第一本著作《书城挹翠录》,“宏烨楼”,为我读书之楼名,“苏斋年谱”系指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翁方纲年谱》,“顾老”即顾廷龙先生。
2005年元月,丁公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为拙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写序及《赵万里文集》事,最后又为我赋诗一首:“长笺序文我未能,纸短情长献愚诚。三十三载欣识荆,敢为宏文添附庸。”并作注云:“1961年赵先生江南访书归来,对我言及沈兄拜顾老为师事,令吾效之。但愚鲁如我,终未能成正果,但此时是识荆之始也。”

丁瑜先生(左)与沈津先生合影
(摄于2019年12月)
丁公和我是忘年之交,在工作中于我时有指导与鼓励,拙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即将出版之际,我曾恳请他作序。不多久,他就将序寄到。序中有云:“余悉沈津先生之名,始于1962年春(津按:1961年11月中,赵万里先生到浙东、闽北、闽东南一带进行图书文物调查工作,历时三月,次年2月25日返回北京),识荆则在十六年后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一役中。《书目》汇编阶段,沈兄文旌北上,居于北京香厂路,任经部副主编,我则忝列丛部,朝夕相处八阅月之久。《书目》定稿阶段,我则南下沪渎,与沈兄同室办公,于业务多所交流,颇得三友之益。”
我还记得在香厂路期间,某个星期天的晚上,他专门来接顾廷龙先生、沈燮元先生和我,去他在德内大街延年胡同的家里吃饺子。看得出来,那天晚上他特别高兴,几杯酒下肚,不仅脸色有点红,话也特别多。2012年冬,我去北京出差,顺道看朋友,其中最想见的就是丁公,也数他年龄最大。他新搬的家还挺远,林小安兄开的车,临近他家,还问了两位路人,方才找到。虽然是近九十的老人,但看上去精神健康,齿德俱尊。他说平时不大出去,怕跌跤,在家也就翻翻书,看看电视里的新闻。询之还做什么题目吗,他笑着说:人老了,不想动了。那天晚上,我们就近去了一家他熟悉的饭店,他的儿子陪同前往。我对丁公说:您想吃什么,尽管点。我知道他酒量不错,但那晚没有要酒,大约也是为了老爷子的健康吧。
丁公是一位高简、淡泊、深藏若虚、与世无争、不求闻达、洁身自好的文化人,这是非常难得的。我很感谢丁公对我的信任,嘱我为他的大著撰序。在他鲐背之年,且进军期颐之际,我也谨祝他“人瑞先征五色云,期颐岁月益康宁”。是为序。
2015年11月15日
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丁公遽归道山,不胜黄垆之痛。忆及去年十二月初,津有北京之行,觅暇探视先生,同行者有曹?? 罗彧 马步青三位博士。先生知我们要去,早早起床等候,并嘱家人出门购水果、饺子之类,见面聊起旧事,先生异常高兴,家人说 父亲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我怕先生累,坐了四十五分钟即告辞。家人持两瓶专门买的好酒赠之,说这是父亲特别关照的。先生于我,感情、感动何须多言,临别时的一声 保重,是最寻常的叮嘱,却成了永诀!而他送至门口的那一瞬间,却成了最后一眼,总以为来日方长,还有见面机会。谁知世事无常,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丁公一路走好 …
沈津2020年6月16日,时客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