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日期:2018-05-04
作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孙显斌
编辑:赵洪雅
在《中国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顾与思考(上)》中,孙显斌老师系统介绍了中国科技典籍的现存数量及整理概况,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典籍的整理成果。书接前文,在今天这篇文章中,孙老师进一步提出了对中国科技典籍的问题与思考,让我们看看孙老师是如何说的吧。
三、问题与思考
这些整理工作为读者提供了方便利用的科技典籍文本和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由于客观条件和整理目标等方面的限制,不少整理成果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缺憾。
首先,一些整理工作使用底本和校勘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章培恒在《关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范化问题——以底本问题为中心》中指出至少有底本选择不善,点校失误;所用底本说明不清;不忠实地以其交代的底本为底本;改动底本文字不说明等几方面的问题。影印本就常常存在所用底本说明不清的问题,如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针灸大成》,整理说明称是“明刊本”,实际上是用清重修本、递修本拼合而成。1961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针灸聚英》排印本称以日本翻刻本为底本,参校嘉靖初刻本,实际上与两种版本都不同,除字句外,篇名、按语都进行了改写而未做任何说明,后来点校明以后的针灸典籍,又均用此排印本做参校本,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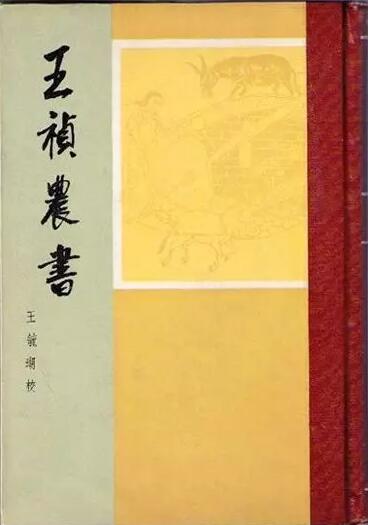
王毓瑚校《王祯农书》
再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囊括了章文指出的种种问题。《王祯农书》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版过王毓瑚的整理本,王氏利用了嘉靖本和四库本两个版本系统,并且给出了大致不错的版本源流情况,应该说是同类整理成果中的上乘之作,这个整理本出版以后,影响很大,比如缪启愉译注本即以此本文字为据。我们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发现王氏的整理本限于当时条件,问题还是不少。比如,按王氏所说文字以四库本作底本,插图以嘉靖本作底本。很遗憾王氏没有指出他用的四库本具体是哪个本子,在王氏整理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本还没有出版,文溯阁本恐怕也难看到,他最可能见到的就是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但是经过我们将文渊阁、文津阁两个四库本与王本比对,发现其与两个四库本都有大量文字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与武英殿聚珍本系统(四库本系统的子系统)相合,这说明王氏起初的工作底本不是某个四库本,而是某个聚珍本系统的本子。王氏后期虽然用文津阁本做了对勘,但做得很不彻底。王本甚至还有一些异文不同于所有四库本系统,而与嘉靖本系统相同的情况。另外,王氏所用嘉靖本最初的工作底本恐怕也是后来翻刻的某一版本,而非祖本。我们经过重新校勘,发现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嘉靖本都优于四库本系统,与王氏的结论不同,嘉靖本的缺点在于有不少明显的讹误,所以初判之下,容易得出“舛讹漏落,疑误宏多”的结论,但是这些讹误多为形近音近而讹,校正并不困难。相比之下,四库本系统经过严格的校改,这种低级失误很少。但是嘉靖本的异文相比之下往往更优,四库本系统则多有妄改。如《谷谱•粟》“早田净而易治,晚者芜薉难出”,“出”四库本作“治”,与通行本《齐民要术》同,此段虽是《齐民要术》文字,却是从《农桑辑要•种谷》转引,嘉靖本与元刻《农桑辑要》同为“出”,并且《齐民要术》金泽抄本亦作“出”。实际上“芜薉”用“出”字表示除去之意更为妥帖,“治”古义是治理的意思,反而不搭配,且有上下重文之嫌。又如《谷谱•大小麦》“惟快日用碌碡碾过”,缪启愉注:“‘快’,各本作‘伏’,后人所改。按本段出于《要术•大小麦》篇,《要术》的两宋本及元刻本《辑要卷二•大小麦》所引《要术》都作“快”,而辑自《永乐大典》的殿本《辑要》作“映”;但查《永乐大典》卷22181‘麦’字下引录王祯《谷谱》也是‘快’,而‘伏’‘映’为后人误改。今按:‘快’是‘好’的口语”。缪氏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受王毓瑚整理本误导,实际上嘉靖本和《永乐大典》引文此处正作‘快’,可能又是四库本系统不解“快日”而误改。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遍阅各版本,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校勘和分析,根据学者的研究,不仅不同的版本之间差异需要重视,甚至不同印次之间有时都有不少重要的差异,而这些信息往往提示了研究该文献的重要线索。随着时代的发展,藏书机构越来越开放,更多的古籍图像得以数字化上网共享,所以在今天的条件下,即使以前整理过的典籍,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和检视。

《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
其次,无论是古籍影印还是排印点校的整理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但同时它们又是互补的。众所周知,影印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典籍的原貌,但是既不方便阅读,也不方便展示点校成果。而做过点校整理的同仁都有体会,百密一疏,再仔细认真也难免出现漏校等问题,以致形成对读者的误导。另外,古籍的书叶里蕴含了更多的信息,这些往往会在排印本中遗失,应该说影印图像和文本点校排印两种整理方式对研究者来说都很重要。这样就有专家指出要想真正达到既整理典籍,又保护典籍原貌的双重目的,必须在整理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现有的条件下,采用影印—排印对照的点校、批注整理方式可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不同水平的整理者可相应地选用不同难度的操作方式。张柏春、田淼、雷恩(Jürgen Renn)、马深孟(Matthias Schemmel)等国际同行合作整理的《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就采取图文对照的版式,将书影与录文、校释文字对照排版,这样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典籍原貌,同时又提供了点校整理成果,方便研究和阅读,将这一理念最先在中国付诸实践。按照这种新的整理方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策划了《中国科技典籍选刊》,以图文对照的方式整理中国科技典籍,提供高质量、可靠的文献整理成果,为学术研究和利用提供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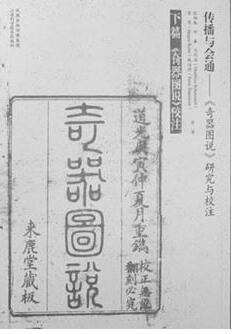

《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中书影、录文与校释文字对照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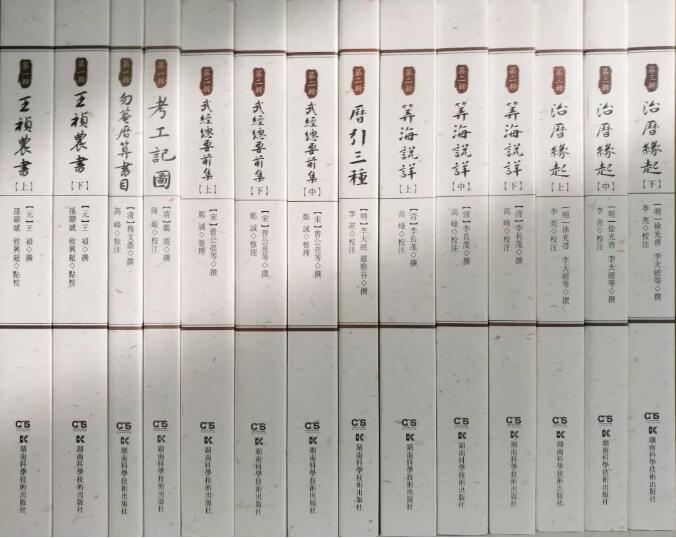
《中国科技典籍选刊》
最后,我们在整理实践中发现被学界遵从的“定本式整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涉及到校勘的目的问题。一般我们都认为校勘的目的是回到“作者”,倪其心指出“校勘古籍的目的和任务是力求存真复原,努力恢复古籍的原来面貌,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这种旨趣正与鲍尔斯(FredsonBowers)、坦瑟勒(ThomasTanselle)提出和推动的“作者意图理论”(authorialintentions rationale)相呼应。这当然是历史研究的必然取向,我们希望还原作者的原稿形态,才有可能最忠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研究该文献。问题还不是我们能否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实际上我们只能也必须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的面貌,真正的问题是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尽管它很基础很重要。绝大多数的文本在流传中都会发生各种变异,这也是我们需要校勘的原因,但是每一种变异的文本都可能有它独立的影响,即有它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就是说每一个文本有它的传播史和研究史。无论是源自法国的“文本发生学”(geneticcriticism)还是麦根(JeromeMcGann)提出的“文本社会学理论”,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最终文本,而是以实证的方式,重建文本形成过程的事件链条。而回到“作者”的文本消除了传播中的文本变异,仅仅依靠它我们对文本的流传和影响将一无所知,有时候反而会被误导而感到困惑。还是举《王祯农书》的例子,它问世后多有流传,影响广泛,通过考察包括《农政全书》在内的十数种典籍的引用,发现全都依据嘉靖本系统,四库本系统诞生后几乎毫无影响。例如《农器图谱•田制门》“区田”:“又参考《氾胜之书》及《务本书》”为《农政全书》所引,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校记称王祯引文作“务本新书”;“诸山陵、倾阪及田丘城上”,石校称王祯引文“丘城”上无“田”字。实际上石声汉依据的是王毓瑚整理的四库本系统,嘉靖本系统与《农政全书》引文全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根据《农政全书》引《王祯农书》的异文特征,可以推断徐光启依据的正是嘉靖本系统。我们暂不论嘉靖本和四库本系统文本的优劣,只讲嘉靖本在历史上的影响,不清楚其面貌,就会像石氏那样因为仅依据四库本系统,得出王祯原书不作此的错误结论。而这正是因为四库本系统民国万有文库本和王毓瑚整理本的出版流行,反使此前流行的嘉靖本淹没无闻了。
通过版本源流的分析,选择最善本作为底本进行汇校的“定本式整理”,对于回到“作者”的目的来说自然是最有效最省力的方式,版本源流提纲挈领,校勘记撰写要言不烦。但是它的局限就在于无法全面展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情况,大量丢失考察文本传播史和研究史的重要线索。因为在“定本式整理”的范式下,对于错误或者意义不大的异文是不需要在校勘记中都繁琐地罗列的,它们无助于还原文本原始面貌。但如果从发生学方面考察,即使不是一个善本,特别是通行本,考察和记录它的异文情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些异文特征可以提示我们在传播中的文本形态,帮助我们揭示各种文本形态的传播与影响。早有学者指出“定本式整理”的这一问题,如乔秀岩(HashimotoHidemi)就指出乾嘉以前与道咸以后,流行的版本有较大差别,道理很简单,乾嘉时期出现的大批古籍整理成果,遂成为后来主要流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自然不是乾嘉学者平常使用的。至于道咸以后学者使用过的书与版本,时间越晚越接近我们现在的藏书。例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耽”字下引《淮南•坠形训》“夸父耽耳在其北”,高诱注“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读衣褶之褶。或作摄,以两手摄其肩之耳也。”高注末句费解,现通行本作“以两手摄耳,居海中”,不言有以上异文,后查张双棣《淮南子校释》才知“王溥本、朱注本”作此,说明段玉裁自有所本,所以校书必须注意作者用过的书和版本。“定本式整理”无法解决这一需求。
当然,有了提纲挈领的版本源流情况,我们一样可以将异文罗列做得高效省力,不需要大量重复地罗列各本的异文,只需要罗列各版本子系统祖本的特征异文就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每种版本在其子系统中例外的异文才须罗列,但是数量不会太多,并且这部分异文罗列不用放在图文对照的页面,可以附在每卷之后或者全书之后,以供查考。
四、结论
现今通行的古籍整理方式的理念和实践肇始于百年之前的“整理国故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古籍整理更是不断制定规划,总结和完善理论,铺开实践,产出了大量包括科技典籍在内的整理成果,但仍有数量巨大的典籍宝藏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理论和实践也需要不断提炼和总结。对于已经整理过的典籍,在今天这样一个学术条件更开放更优越的时代,也需要重新评估和检视。根据整理古籍的实际经验,我们提出一种典籍整理的新范式,称之为“图(像)定(本)异(文)参照式整理”。这一新范式反映了我们在典籍整理中希望贯彻的“三心二意”:三处用心,即影印最大限度保持典籍原貌的图像,配以对应的标点文本和校勘成果,最后辅以各版本的特征异文;两个用意,即回到“作者”的文本还原和文本传播的发生学网络。也只有这样才足以支撑我们对典籍全面的历史的研究。
(本文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56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