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扼江海交汇之要冲,山川雄秀,物阜民丰,尤称人文荟萃,典章焕然。魏晋、隋唐以降,随着几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地区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及至宋室定都临安,则形成了人民之众、财赋之殷,甚于他州的局面,文教随之昌隆、人才随之鼎盛,名贤巨擘遍布全省,达到了“列郡踵继,无邑不有”的地步。许多州县都是著名的才子之乡,或著作宏博,或富于庋贮。名楼大阁遍地生花,公私藏书俱称浩繁。

宁波天一阁入选首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之一
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促成了今天浙江在古籍资源分布上的突出地缘特色,即数量多、价值高、分布广。据已经完成的全省古籍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古籍存藏总量近22万部,民国线装书11万部,藏书总数在全国名列前茅。古籍中多珍罕善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者就有871部之多,“南三阁”中硕果仅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历代浙江籍历史名人的稀见稿抄校本,尤称珠联玉映,熠熠生辉。浙江省古籍存藏单位多达95家,几乎是县县有古籍。县级图书馆、博物馆里不乏海内孤本,中学校园的藏书也钤印分明、传承有绪。
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地缘特色,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始终以“将传统乡邦文化根植基层土壤,让珍贵古籍资源发挥现实作用”为指归,以全省古籍普查为核心抓手,配合以人才培养、古籍修复、古籍存藏环境建设、古籍阅览服务、古籍整理出版、古籍知识宣传推广等多元手段,上下一盘棋,全面、系统开展全省古籍保护工作。
古籍普查 文化担当
全面、系统、高质量完成全省古籍普查,是浙江省10年古籍保护工作的突破口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古籍普查,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存世古籍进行全面“清点”。其目的在于通过每部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和相关信息,建立国家古籍登记制度,加强各级政府对古籍的管理、保护和利用。一方面,古籍普查是一项嘉惠当代、泽被千秋的基础性工程,是当代文化工作者承先贤业、为子孙计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将分散在各地、各系统、各单位的千百万册古籍一一清点,登记信息、上传书影,是水滴石穿的艰巨工作,做起来覆盖面广、专业性强、耗时费力、见效不易,非组织严密、持之以恒、群策群力不能为也。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选择以普查作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核心项目,颇有近代浙江籍儒学大家马一浮所称“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意味。截至2017年4月底,浙江全省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文脉得以揭示。
在古籍普查工作开展之初,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并下达了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标准,要求广大古籍普查员将古籍的索书号、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式、装帧、装具、序跋、刻工、批校题跋、钤印、丛书子目、定级、定损、书影16个大项一一著录明白,为下一步编写《中华古籍总目》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要求的提出主要基于大型古籍存藏单位资深专家的既有古籍编目经验,对基层单位人员、经费紧缺,特别是普查员专业化程度很低的情况考虑不足。因此,这一要求甫经实践,就让各基层单位产生了畏难情绪,普查进度缓慢。于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古籍普查必填项目减少到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存缺卷数6项,原定的其他项目作为拓展项,允许各单位根据自身情况选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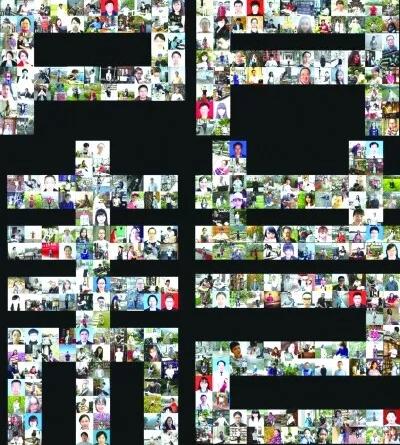
2017年9月浙江“古籍编目工作研讨会”会标
浙江虽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但在2007年以前也存在基层普查力量薄弱的问题。浙江的地市级图书馆古籍存量多在5万册以上,一些单位甚至达到15万册,但专门从事古籍整理、保管、修复、服务工作的馆员只有几个人,具有相关专业背景、能够独立完成古籍普查的就更少。县级单位少则几百册,多则几千上万册的古籍,大多没有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具有专业水准的普查员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全省上下始终坚持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早提出的16项著录标准完成古籍普查,并由省古籍保护中心为各单位配发照相机、扫描仪等设备,确保为每部普查过的古籍留下清晰书影。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省图书馆馆长徐晓军将这一份迎难而上的坚持戏称为“一条道走到黑”。
普查要求明确后,浙江省内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感到压力很大,纷纷向省古籍保护中心提出,本单位没有能够完成古籍普查的相关专业人员,藏书不多,能否请省图书馆派人代为完成。对此,徐晓军明确表示:“普查责任必须到县到人,省图可以做培训,但绝不代劳。”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浙江全省开始了“培训+普查”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按照省古籍保护中心要求,各基层单位派上几名馆员,人手一张火车票,买上一套铺盖卷,就入住了位于杭州市中心的省图书馆宿舍楼。这些基层馆员大多不具备文史专业背景,也没有从事过古籍相关工作。但徐晓军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基层馆员只要受过高等教育,无论什么专业,都可以派来,我们保证教会。”不但人到,还要书到。一些小馆的参训人员甚至随身搬来了本馆的全部“家当”,书先做杀虫处理,再带进培训现场。此后长则一个月,短则十来天,参训人员在省图专业古籍编目员的耳提面命下,以本馆的古籍为实践对象,从零开始,边学边做,完成的数据质量经省馆老师审校认可,即可算作“毕业”。

云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小微书库”内整理本馆古籍
位于浙西南山区的云和县图书馆只有7名工作人员,且人人“外行”,面对本馆堆砌一隅的3000多册线装书,馆长潘丽敏一筹莫展,极力请求省馆代做普查。而徐晓军则予以坚拒,执意要求云和馆到省图培训。二人争执不下,潘丽敏还为此掉了眼泪。2013年春节前夕,潘丽敏带着两名馆员和本馆的古籍来到省图参加培训,像小学生一样从零学起,到培训结束时已届除夕。不过,也正是通过这个机会,潘丽敏和她的馆员们开始喜欢上古籍,不仅是古籍普查,还有古籍的整理、修复、展览宣传,特别是古籍背后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2013年11月,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山区小县云和成为浙江全省第一家完成古籍普查的单位,并在普查中发现了一批本地区特有的稀见家谱、畲族文献和道教抄本。2015年10月,《云和县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图目》出版,云和县图书馆成为全国较早独立出版配带高清书影普查目录的县级图书馆。
“传统文化这一课,基层文化工作者、管理者过去是欠缺的,只有亲自动手做过古籍普查工作,他们才更能产生文化使命感,更有文化担当。基层馆的普查由省馆代做是很容易的,我们舍易求难,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但收获的影响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回顾10年普查,徐晓军如是说。
(转载自《中国文化报》2017-12-14)



